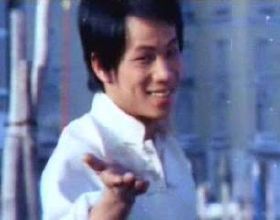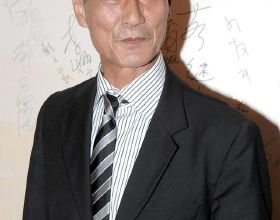在浩瀚的古體詩創作花園中,格律詩算是一朵馥郁的花朵。經過歷代詩人的不懈探索,格律詩的形式日臻成熟,成為一種獨特的詩體。格律詩的基本要求應該是平仄合律,對仗工整,主題鮮明,意境悠深。有的文人刻意挑出種種所謂“詩病”,來制約格律詩的創作,就像一道道繩索束縛著格律詩的發展。什麼“摞眼”,,什麼“撞韻”,“不能用成語”,“不能有重複字”,不能“擠韻,”。這本來是一己之見,現在有的詩刊編輯動不動以這樣所謂詩病評價詩作,以有詩病的理由不發表作品,還有的詩群裡的詩詞教師也大講特講這些詩病,以此炫耀自己的博學。而他們寫出的詩作卻東拼西湊,言之無物,味同嚼蠟。我對這些所謂的詩病很不以為然。我認為一首格律詩在平仄合律,對仗工穩前提下,重要的是看主題是否鮮明,是否有內涵,是否跟上時代的步伐,是否有新穎的詩句。如果詩作表現出深刻的哲理,那是最好的。而強調所謂的詩病只能起到束縛格律詩發展的作用,我認為應該解開這些束縛格律詩的繩索!現在逐一對詩病的荒唐之處加以剖析。
“摞眼”真佩服那些老學究怎麼想出個詞來命名詩病。“摞眼”,摞即疊的意思,就是一般指詩的中二聯四句中的眼字在同一位置像物體一樣向上疊起來了。有的人在詩群中講到格律詩時一再強調中間四句前兩字不能用名詞,用名詞就是“摞眼”,不能承轉起合,是寫詩大忌。我對此說法很不以為然。我舉兩首詩為例。一首是毛澤東的七律《長征》,其中的“五嶺”“烏蒙”“金沙”“大渡”,全是名詞,可是我們讀起來沒有一點不好的感覺,只感到和諧順口。還有一首文天祥的七律《過零丁洋》其中“山河”“身世”“惶恐灘”“零丁洋”也都是名詞,我們只感詩構思的精妙,沒感到對詩的藝術性有何削弱。而且這兩首詩都是驚天地泣鬼神的不朽之作,足以千古流傳。而那些喋喋不休大講“摞眼”的人所寫的詩其內容其意境與這兩首詩相比天地之差!有的論述“摞眼”的文章也承認“摞眼”之病並不違反詩詞格律,所以算不上什麼大病,完全可以忽略。
“撞韻”。撞韻現象無論在古人還是現代人的詩作中頻頻出現,多不勝舉。“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頭顱早悔平生賤,肝膽寧忘一寸丹。”“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這些所謂“撞韻”之句,不但沒有對詩的意境有任何影響,還產生了獨特的音韻效果,使之成為心口相傳的名句。所以“撞韻”一說,完全站不住腳!
“不能用成語”成語是我國經過長期總結流傳,皆有典故的獨特語言表達形式。適當應用成語,有利於精準描述事物,表達感情。格律詩受格式的限制,要用精準的語言表達思想與情感,適當運用成語可以令詩錦上添花。毛澤東《長征》中“萬水千山”《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中“虎踞龍盤”“天翻地覆,”魯迅詩中的“橫眉冷對”“漏船載酒”等成語的運用都恰到好處,為詩增色不少,那種格律詩不可用成語的說法很沒有說服力,應該休矣!
“重字”格律詩限於字數要求,應避免用重字,這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必成為絕對清規戒律。“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毛澤東《長征》中“千”“山”“軍”“水”字都重字,也沒影響詩的氣勢。順便說一句,羅元錚教授致信毛主席,他認為詩中有兩個“浪”字,建議將“浪拍”改成“水拍”,毛主席同意了並稱羅元錚為“一字師”。可是兩人都忽視了一點,那就是“浪”字不重複了,可“水”字也重複。而且“水拍”不如“浪拍”響亮生動形象。我看過幾首步韻《長征》詩,雖無重複字,但很小家子氣,在氣勢與意境上與《長征》相差很遠。這說明,有重字也不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欣逢盛世,我們就要為時代謳歌,抒情詠志,而不要在詩中寫自己寫醉生夢死的生活,抒發灰色情懷,表達那種生不逢時,懷才不遇的消極情緒。無論古風,還是格律,都應服務於火熱的生活,描寫祖國大好山河,描寫英雄人物,描寫真善美,抨擊假惡醜。讓古體詩真正煥發青春。不久前我曾寫七律一首,表達我對寫詩的一些想法,引用於此,作為小文結束句。
寫詩偶感
恨病糾纏痛伴隨,
傾心創作願高飛。
精搜古韻研今律,
細索新詞納舊規。
吐露情懷求境美,
清除桎梏願詩瑰。
人生有際學無限,
羈旅迢迢志不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