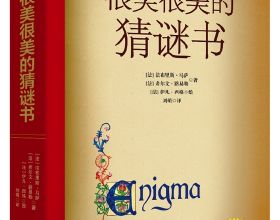近代西方前所未有的科技和經濟繁榮究竟是何時開始的,以及為什麼開始的?
曾以“四大發明”饋贈歐洲,並以鄭和艦隊七下西洋之壯舉傲視天下的東方,又是何時衰落的以及為什麼衰落的?
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為此提供的各種解釋充滿了書架,其核心不外乎試圖解釋為什麼“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都發生在西方而不是東方。一個顯而易見的共識是:正是這兩場革命,徹底改變了歐洲和人類的歷史命運,成為近代“東—西方大分流”的分水嶺。
但究竟是什麼因素促成了這兩場革命的爆發?當前國內外十分流行的歷史觀(包括強調“路徑依賴”的新制度經濟學)認為,關鍵是制度。
按照這種歷史觀,正是古希臘獨有的民主制度與理性思維傳統,以及古羅馬和日耳曼部落遺留的獨特法律制度,一同奠定了近代西方科學與工業文明賴以產生的制度基礎,從而在文藝復興以後演變成一種不同於“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的民主議會制度和法治社會。這種包容性議會政治制度和法治社會,決定了包容性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產生— 比如契約精神、人性解放、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和對專制王權的限制,因而有效降低了各種市場交易成本(包括思想市場和商品市場的交易成本),激勵了國民財富的積累和科學技術的創新發明,導致“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這兩場革命的爆發。
這種歷史觀如今在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如此流行和“不證自明”,以至於需要我們對西方近代史從頭到尾、從裡到外、從下到上、從微到著去重新審視和批判,才能發現它的破綻。
歷史觀,無論正確與否,對學界、商界和政界的影響遠比人們想象的要強大。正是因為這種“西方中心主義”歷史觀統治著世界,才造成落後國家的知識精英、 企業家和政治家對當今世界的變化迷惑不解,以至於在面對來自“先進發達”的西方世界的意識形態壓力時,在思想和行動上顯得蒼白無力、無所適從、愛恨交加。而那些誤以為自己不受任何歷史觀影響的精英集團,實際上都是某種歷史觀的奴隸,並每天都在以西方灌輸的歷史觀理解和創造著自己國家的歷史。
但是,經過西方上百年打造形成的這一流行歷史觀,卻與幾千年來人類文明的真實發展史嚴重不符。
首先,與流行歷史觀所肯定的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至少同樣輝煌的,還有同時期的中華文明和印度文明,以及稍後的阿拉伯文明。如果古希臘“民主”和古羅馬“法制”一直是西方經濟與科技繁榮的根基,而衡量經濟與科技繁榮的最佳標準,不外乎人們衣食住行所反映出來的生活水平—因為它直接反映了一個文明體系的生產力和服務於這個生產力的深層制度,那麼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生活水平就不應該低於而是應該遠遠高於同時代的中國。為什麼?因為按照西方中心論和新制度經濟學的邏輯,只有比同時代中國更高的生活水平才能折射出比中國更加發達的生產力和更加優秀的政治與經濟制度。
但事實是,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生產力通常都比中國低下,更不用說歐洲中世紀甚至整個文藝復興時期的生產力。
比如以煤炭作為替代木材的新型能源,在歐洲是中世紀後期和文藝復興初期才發生的事情。相比之下,煤炭在中國的使用和開採已經有4000多年的歷史,而用於鍊鐵也可以至少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也就是2500多年前。對此,18世紀啟蒙思想先驅,卓越的歷史學家、哲學家和文學家,歐洲近代史上最才華橫溢的既精通古希臘又通曉18世紀自然科學的思想大師伏爾泰,在論述煤炭、鍊鐵和中國古代的其他科技成就時說道:“早在四千年前,我們還不知道讀書寫字的時候,他們就已經知道我們今日拿來自己誇口的那些非常有用的事物了。”
對此,法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年鑑學派領袖人物布羅代爾惋惜道:“中國燒煤(和鍊鐵)的歷史雖然如此之早,……強盛的中國本來具有開啟工業革命大門的條件,而它偏偏沒有這樣做!它把這個特權讓給了十八世紀末年的英國。”
伏爾泰和布羅代爾都不是唯獨這樣對西方與東方早期的巨大“逆向”差距感到疑惑的西方歷史學家。公元前5世紀的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曾經同樣追問:“是什麼將歐洲和亞洲區別開來?”希羅多德想知道的,是為什麼西方落後而東方先進。他所知悉的東方,位於地中海和印度恆河之間,這裡居住著許多不同的民族。他認為亞洲土地肥沃,城市繁榮,人民豐衣足食、舉止文雅;而貧窮的希臘和希臘人完全無法與其相提並論。
比如古希臘人穿的衣服,普遍由粗麻織成,是很少染色的沒有領口和袖子的簡陋披肩和裹身粗布;而同時代中國人穿的衣服,卻是由細得不可思議、輕得不可比擬的蠶絲,透過木製織機細密織成,再用五顏六色的有機染料層層上色,經過千針萬線裁縫而成的綾羅綢緞。縫製衣服需要金屬針和剪刀,沒有發明鐵或者金屬冶煉技術的文明很難用木材、石料或者骨頭做成剪刀或細小的刺繡針,而中國的絲綢技術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時期。如果那個時代有什麼精密工藝能夠形象地體現公元17世紀牛頓和萊布尼茨的微積分運算之精妙的話,非中國絲綢的製作過程莫屬。
絲綢產業所體現的生產力和文明程度可不簡單,它涉及原材料產業(桑樹的栽種、蠶卵的儲存、幼蠶的哺育、蠶繭的保管與漂白),紡織業(抽絲剝繭、紡絲織布),染色業(染料的萃取、化工製作和對大批次絲綢的均勻上色),成衣製作業(剪裁、縫製、上扣、打邊、刺繡),原始的市場營銷業(服裝樣式設計、訂單、發貨、統購、零售),等等。而且這樣精細的工藝流程與分工環節只有統一的大市場和信用體系才能支撐,絲綢製造業不是任何古希臘城邦小農經濟輕易能夠拓展與承擔的產業。難怪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創造運河體系和最早發明造紙、印刷、陶瓷、火藥、指南針、現代官僚制度和發行紙幣的國家。只有高度發達的大一統市場經濟與信用體系才可能流通紙幣。而歐洲國家要等到18世紀才開始出現紙幣。
即便到了輝煌的古羅馬帝國時期,全球財富的主要創造中心也仍然在東方。這從當時的東—西方商品進出口結構中可以看出。古羅馬時期沒有任何商品(除了黃金)值得出口到遙遠的東方,而古羅馬最珍貴的進口商品卻一定來自遠東,這包括比黃金還要貴重的中國絲綢。在古羅馬,只有皇帝和最富有的官員才能偶爾穿得起絲綢。比如羅馬皇帝埃拉加巴盧斯(Elagabalus),儘管也會穿當地亞麻做的簡陋粗布衣服,但卻是西方歷史上第一位有錢在全身上下都穿得起來自東方的綾羅綢緞的西方人。
羅馬人稱中國人為賽里斯(Sērēs)人,也就是絲國人。古羅馬與秦漢時期的中國商人,透過“絲綢之路”與義大利半島、巴爾幹半島、地中海海域以及中東的希臘人、羅馬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展開貿易。也正是這些地區對中國商品的巨大而持久的需求,形成了橫貫歐亞大陸和印度洋的古絲綢之路。經由絲綢之路,不僅是絲綢,其他商品諸如光滑如玉、細膩如肌的彩釉陶瓷也被源源不斷運出亞洲。斯里蘭卡曾經是連線東亞和地中海的一個重要貿易據點。拜占庭編年史作家科斯馬斯 · 印第科普萊特斯寫道:“許多船從印度、波斯和衣索比亞彙集到這座島嶼(即斯里蘭卡)……還有從更遠的地方來的,我指的是秦尼斯(Tsinista,即中國)。”
英國曆史學家和古絲綢之路專家弗蘭科潘指出,為了購買東方奢侈品,尤其是絲綢,古羅馬每年有多達1億賽斯特斯(sesterce,古羅馬貨幣單位)的金幣從羅馬帝國流出,進入東方貿易市場。“這一驚人數字相當於帝國每年造幣總數的近一半。”“絲綢作為一種奢侈品的同時,還成為了一種國際貨幣。”“從某種意義上講,絲綢是一種最值得信賴的貨幣。”
即便從公元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時算起,直到大約1800年工業革命爆發時(也就是直到中國清朝開始由盛而衰的時期)為止,全球最大商品交換和工藝品製造中心仍然在東方,尤其是中國。在那個歐洲開始發生鉅變的300年(1500—1800)間,全球貨幣的流向仍然是中國。每年歐洲人從美洲盜取的天量白銀,大約一半流向了中國,為的是購買中國的商品。比如17世紀一位葡萄牙商人在一篇關於白銀的論文中指出:“白銀在全世界到處遊蕩,最後都流入中國。它留在那裡好像回到了它的天然引力中心。”
布羅代爾對此感嘆道:“貴金屬不斷從西方流向印度和中國。遠在羅馬時期已經出現這種情況。必須用銀子或金子購買遠東的絲綢、胡椒、香料、藥物和珍珠,否則西方得不到這些貨物。西方與遠東的貿易因此一直有逆差,就西方與中國的貿易而言,這一逆差維持到19世紀20年代(也就是工業革命爆發半個世紀以後)。這是一種經久不息的結構性流失:貴金屬透過地中海東岸地區,透過好望角航路,甚至穿過太平洋,自動流向遠東。”就連因與遠東保持緊密商業往來,主導絲路貿易的廣大中亞與阿拉伯地區,也由此經歷著長期的繁榮。
為什麼?因為即便在牛頓科學革命爆發以後很長時間而且直到英國工業革命初期,“中國在世界市場上(仍然)具有異乎尋常的巨大的和不斷增長的生產能力、技術、生產效率、競爭力和出口能力,這是世界其他地區都望塵莫及的”。“中國憑藉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以匹敵的製造業和出口和任何國家的貿易都是順差。中國製造業在世界市場上具有高產出、低成本的競爭力,所以中國能夠有效地給世界市場提供商品供給”。
相比之下,號稱繼承了古希臘與古羅馬文明的近代基督教歐洲,在工業革命之前其生產力的低下和日常用品的匱乏程度,遠超今天人們的想象。就拿穿衣、吃飯和如廁來說。在中華文明經歷好多輪盛極而衰、衰極而盛的長週期之後,普通歐洲人穿的仍然主要是由粗羊毛編織的裹身披衫。這種粗羊毛布料容易藏汙納垢,很難用水清洗,因此歐洲人一輩子很少換洗衣服。由於非常粗糙並刺激面板,這種布料無法用來製作內衣,所以普通歐洲人自古以來直到工業革命前都幾乎不穿內衣,也不知道什麼是內衣。與此相比,絲綢非常貼身,既可做外衣也可以做內衣,還可以做手絹、扇子、畫布、屏風、蚊帳、桌布、窗簾、床單等日常用品,因此受到萬里之外的古羅馬皇帝的青睞。
由於沒有發明紙張、絲綢和棉布,直到工業革命前,歐洲無論男女、老少、貴賤,一輩子如廁時都沒有條件清潔下體。而且吃飯都是用手抓;吃飯用的叉子要到17世紀才開始在歐洲家庭普及(美國白人甚至直到19世紀初才開始用叉子吃飯)。因此著名歷史學家蘭德斯(1999)對於歐洲人在工業革命前的衛生與生活水平有如下描述:
長期以來,歐洲人最大的殺手是胃腸道感染,病菌從人體排洩物傳播到手,再到食物,再回到消化道。霍亂病菌等流行性微生物不時加強了這類看不見卻致命的敵人的存在。這些細菌最好的傳播途徑是公共排洩地:在那裡,由於缺乏廁紙和可換洗的內衣而促進了人體與排洩物的接觸。由於長年累月都裹在一輩子都沒有洗過的粗羊毛布中,而粗羊毛布料很難清洗,即便洗也洗不乾淨,因此歐洲人的面板常會發癢並不得不用手抓撓。所以他們的手很髒,而最大的錯誤是歐洲人在進食前都不洗手。……而工業革命改變了這一切。工業革命的主要產品是東方傳來的既便宜又可用水清洗的棉布,以及靠規模化大生產方式從植物油中提煉出來的肥皂。普通人第一次買得起內衣……個人衛生狀況的巨大變化,使得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歐洲平民可以生活得比一百年前的國王和皇后還乾淨。
難怪即便到了英國工業革命初期的1776年,亞當·斯密也還承認“中國比歐洲任何地方都富有”。
美國曆史學家戈德斯通也說:“中國是很多產品在全世界最早的生產國,包括紙張、火藥、帶有船尾柱舵輪和水密隔艙的航海船隻、指南針、三角帆船、鑄鐵工具以及精美的瓷器等等。印度也為世界提供了色彩絢爛的奢華的棉織品。中國和波斯還是世界上絲綢工藝首屈一指的地區。當印度人和中國人穿著柔軟舒適的棉織衣物時,歐洲人還裹在粗糙的亞麻和羊毛衣物裡。”
著名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也承認:“在中古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的更先進和更優越。”
因此,一個毋庸置疑的歷史事實是,從古希臘直到第一次工業革命爆發初期,中西方在生產力和國家治理能力方面的早期差異一直十分突出;一直要到近代18—19世紀才開始逆轉,那時候歐洲的科學、技術、國家治理和國家動員戰爭的能力才開始全面崛起,從而超越東方文明。
由此可見,流行歷史觀強調的古希臘包容性民主自由傳統和日耳曼部落的法律文化,並沒有如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所預言的那樣,為古希臘、古羅馬、歐洲中世紀、文藝復興以後的義大利,直到工業革命爆發前夕的整個西方世界帶來超越東方的生產力水平與經濟繁榮。
為什麼?
因為流行歷史觀和新制度經濟學對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為什麼發生在西方的解釋,不僅採用了錯誤的制度衡量標準 ,而且顛倒了政治制度與經濟基礎之間的因果關係。
比如新制度經濟學理論認為,政治制度決定了市場交易成本的大小,交易成本依次決定了經濟的績效和增長速度;因而經濟越發達的國家,其政治制度也越先進;而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公權力與法律制度。
這種理論至少可以追溯到著名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 · 韋伯(Max Weber)。比如韋伯從對法律程式的形式正義(formal justice)和實質正義(substantive justice)的概念區分出發,闡述了資本主義為什麼誕生在西方而不是東方的根本原因。
韋伯認為,在“形式正義”下,當發生私人間的法律糾紛時,法律裁定及其程式均依照一系列普遍的、事先明確規定的規則和程式來進行;與之相對,在“實質正義”下,人們對每一個個案都追求實現最大公正和平等,而且要考慮到法律、道德、政治與各種綜合因素。形式正義可提供高預期性和可計算(predictable and calculable)的法律結局,儘管對某些個案的裁決可能會與實質正義者所根據的宗教與倫理原則或者政治權宜相沖突。由於形式正義減少了個人對統治者的恩惠與權力的依賴,它扼制了獨裁或暴民政治的滋長;而形式正義恰好是歐洲的法律傳統所獨具的。歐洲的法律機構是高度分工的且與政治權力分離的,其特徵是存在自治的、專業化的法律職業階層。法規是運用理性制定的,不受來自宗教或其他傳統價值觀的直接干涉。因此在韋伯看來,脫胎於古羅馬法律傳統的這種程序正義,提供了法律實施過程中的“可計算性”和“可預見性”,因而是作為資本主義文明基石的私有產權保護制度得以在西方而非其他文明中產生的根本原因。
韋伯的觀點滲透到人文學科的所有領域並影響了好幾代西方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法學家和他們關於東西方文化差異的理論,包括今天流行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和西方中心主義歷史觀。哪怕那些長期研究東方古代歷史文化的西方專家也不能免疫。比如東亞與中國史專家埃德溫·雷紹爾(Edwin O. Reischauer)和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談到東西方文明的制度差異時曾經說道:
法律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榮耀,但是在中國,兩千多年來所有法律都被視為可鄙的名詞。這是因為中國法家的法律概念遠遠落後於羅馬。在西方,法律被視為上帝或自然更高秩序在人類世界的具體表現,而在中國,法律僅僅代表統治者的意志。中國幾乎沒有發展出民法來保護平民,法律大部分是行政性的和懲罰性的,也是人們竭力避而遠之的。西方民眾認為比起由容易犯錯的個人來判決,被非人格化的法律管理更加安全。而中國人可能是出於孟子人性本善的觀點,認為被高尚的管理者來統治比被獨斷的非人格化的法律來統治更加安全。
即便我們暫先接受雷紹爾和費正清的說法,那麼他們描述的這種東西方之間法律制度的差異究竟是怎麼產生的?這種差異如果存在的話,真的是“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爆發在西方而不是東方的原因嗎?
首先,姑且不談古羅馬的法律體制究竟是否比中國古代的法律體制更先進和優越,即便是文藝復興以後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法治,雖然表面上依靠法庭和律師制度來維繫,但實際上都是由軍隊和國家暴力來維持的。歐洲國家的專業警察制度,是工業革命很久以後才成熟起來的。因此,工業革命前的歐洲國家,無論是形式還是實質上都是靠軍隊來捍衛法律和社會秩序。
這是為什麼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利,在談到他親身經歷的資本主義萌芽與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法律制度時就精闢地指出過:“沒有優良的軍隊,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有優良的軍隊,就一定會有良好的法律。”而且,馬基雅維利在研究古羅馬時期的法治和社會秩序時也敏銳地觀察到:“在有優良軍隊的地方肯定有良好的秩序。”

羅馬帝國常備軍團士兵(14世紀中後期) 羅馬帝國常備軍團士兵(14世紀中後期)
因此,可以設想即便是今天以法治著稱的美國,表面上它的法治是依靠美國憲法和大法官制度來維持的,但實際上,要是沒有強大的美國軍隊和專業警察系統(包括聯邦調查局),美國根本無法捍衛它的憲法和法庭的尊嚴。反過來,已經在20世紀90年代就採納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烏克蘭,無論其新憲法如何強調三權分立和法治,這個國家一直到目前為止都很少有法治可言——因為它的國家機器和國家能力已經在執行華盛頓共識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徹底瓦解;沒有了優良的軍隊和警察部隊,它的民選總統一個比一個貪腐違法,卻根本得不到法律應有的追究和制裁,使得烏克蘭憲法淪為一個擺設。
正如政治理論家阿爾加羅蒂所說,馬基雅維利“對政治和國家事務正如牛頓在物理學和自然奧秘上那樣具有深刻的洞見”。可悲的是,馬基雅維利這位政治科學大師雖然早在500年前就已經對西方法治與國家暴力的關係做出了精闢分析,而19世紀以後直到今天的歐洲中心主義學者們(包括韋伯)卻依然無法看清歷史的真相。
其次,韋伯的先輩——18世紀德國思想家、歷史學家和文豪——弗里德里希·席勒,早就針對日耳曼人在17世紀所擁有的所謂古羅馬法治傳統的任意不公時精闢地指出過:
“在帝國最高法院,德意志諸等級是自行其是的,因為它們自行聘任法官。他們自行審判,能產生同樣的公正,這也是創辦者的意圖所在。由天主教法官和皇帝走狗操縱的法庭維護的當然是天主教和皇帝的利益,犧牲了公正。”
恰如馬克思指出的:“對‘神聖的所有權’進行最無恥的凌辱,對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只要這是為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所需要的,政治經濟學家就會以斯多葛派的平靜的心情來加以觀察。”韋伯正是這樣一位善於以斯多葛派心情來思考政治經濟學問題的社會學家。
再次,深諳歐洲歷史的啟蒙主義時期思想家,比如伏爾泰和安克蒂爾—杜伯龍,堅決否認歐洲這種杜撰出來的東西方制度差異。伏爾泰很不耐煩地對那些爭論說古代中國沒有法律的歐洲知識分子說道:“不管你們怎樣爭辯伏羲以前的十四位君王,你們的動人爭論只能證實中國在當時人口很多,法律已經盛行。現在我問你們,如果一個聚族而居的民族,有法律、有國君,難道就不需要有過一個燦爛的古老文化嗎?請想一想需要多少時間、若干場合的湊巧才能在礦石裡發現鐵,才能把鐵用在農業上,才能發明織梭和其他一些技藝呢。”
在伏爾泰看來,歐洲歷史上的封建時代(包括他所處的歐洲啟蒙時代),其專制程度和亞洲的統治者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一次又一次問道,東方的編年史作者又會如何看待歐洲的封建體系?它看起來難道比我們描述的東方普遍存在的人身依附程度更低嗎?伏爾泰說,認為東方國家的臣民都是皇帝的奴隸,他們一無所有,他們的財產和他們自身都是屬於主人並可被任意剝奪的,這樣的假設是非常荒謬的;這樣的統治方式只會導致自身的毀滅。而中華文明已經生生不息延續了好幾千年。
安克蒂爾—杜伯龍還專門在1778年(工業革命初期)寫了一篇名為《東方法制》的論文,以此證明西方那個時代剛因全球殖民擴張而獲得一點自信後產生的大量以東方為主題的文字和觀點,不僅充滿了對東方的誤解,而且還存在著某種傾向,將某種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缺陷,甚至是自然因素造成的結果,歸咎於東方國家的“法律制度”和“政府”,以從理論上證明東方文明天生就應該成為歐洲殖民主義者統治或治理的地方。他譏諷地寫道:
亞洲所有的錯誤總是政府造成的。蝗蟲使一個地區受災;戰爭使另一個地區的人口減少;缺雨導致的饑饉逼迫一個父親賣掉自己的孩子(1755年我在孟加拉親眼見過)。下一次發生時,還是政府造成的。旅行家在巴黎、倫敦或阿姆斯特丹寫下自己的作品,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說出任何批評東方的話。而當他們自己的國家發生同樣的災難時,他們將其歸於天氣或人們的惡意。
遺憾的是,這個240年前的評論對今天的西方中心主義者和新制度經濟學家們仍然適用。
哲學家萊布尼茨也與杜伯龍和伏爾泰持同樣的觀點。“對萊布尼茨而言,中國人不僅是偉大的匠人和天才的設計師,他們也是一個非常重視道德的民族。倫理學是他們真正的力量源泉,他們的倫理學中幾乎不包含形而上學和神學的空想,而是堅持教育和對話。”伏爾泰也堅持認為,“中國人是歐洲人反覆嘗試卻一直無法成為的那種人,即真正的道德主義者和斯多葛主義者:‘他們的道德準則非常純粹和嚴厲,但同時又和愛比克泰德宣揚的準則同等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