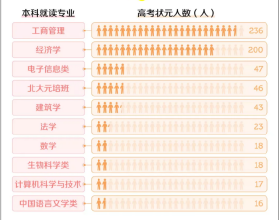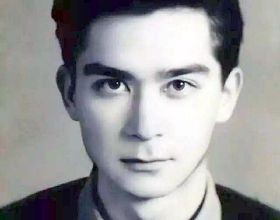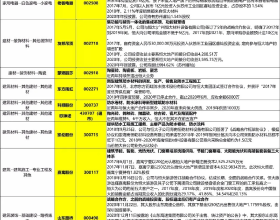在《新唐書》中,專門記載了當時服妖的一些逸事。
所謂服妖,就是衣服穿戴等不符合規制,不合禮儀。
古代視禮節為國家大事、朝政的根本,雖然看上去小題大作,實際就是透過一套繁複的禮儀(包括穿什麼衣服,乘坐什麼樣的車子出行,住在哪種樣式的房子裡等),來確定尊卑等級,禁止逾越,也就是跨越階層,尤其是從平民到皇族的階層。
不過,雍容大度、包容性極強的唐朝,服妖就是一種挑戰傳統的自由發揮,無論文臣武將、公主后妃,都有一顆勃勃生機的不安份的心,想要在人群中彰顯不同。
“唐初,宮人乘馬者,依周舊儀,著冪釭,全身障蔽,永徽後,乃用帷帽,施裙,及頸,頗為淺露,至神龍末,冪釭始絕,皆婦人預事之象。”
這段話說的是唐初的時候,宮女們騎馬是採用的周代禮儀,頭上戴著冪釭,將全身都遮得嚴實。
這個冪釭,可能是一種布做的圓形像桶似的罩子,將頭頸遮得嚴密,以確保穿戴這東西的女子面貌不被人看到。
而永徽後(唐高宗年號),宮女們開始戴帷帽,垂下的帷巾長度只到頸部,以方便女子掀起紗巾露出花容月貌。
不過,此時的冪釭與帷帽還是並行的,兩樣都有,不同的女性,有不同的選擇。
而到神龍末年(武則天年號),冪釭已經絕跡了,沒人再戴這種落伍過時的帽子。
著史書的人認為,這就是婦人干政的預兆。
其實,這未嘗不可以看作女子更加獨立自由的現象,當女子不再被約束於閨閣門戶時,自然就會有更加迫切的展現其美麗的需求。
當時的女子,不僅不懼於在陌生人面前展露面貌,而且還喜歡穿著男裝,以英姿勃勃的形態遊走於宮廷。
“高宗嘗內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帶、皂羅折上巾,紛礪七事,歌舞於帝前。帝與武后笑曰:‘女子不可為武官,何為此裝束?’近服妖也。”
這段說的是唐高宗與武則天的女兒太平公主,曾經穿著紫衫、玉帶,皂羅折上巾,並且帶著紛礪七事,在帝后面前表演歌舞。
太平公主這一身打扮,是武官裝束,唐朝以紫色為高官服色,因此紫衫、玉帶是朝廷高階官員的專屬,而紛礪七事是當時遊牧民族常掛在衣帶上的七件小物件,可以理解為今天的瑞士軍刀套件,小刀、打火機啥的,方便野外露營,所以才說這是武官裝束。
太平公主這一身男裝,還是武裝,自然收穫“服妖”的評價。
不過,放在今天,女性打扮中性卻是一種時尚,甚至還能收穫大批粉絲,以衣著分男女,說到底還是觀念被束縛,狹隘了。
而女性追求男性特色的衣著,無非也是對自由、獨立、自強的嚮往罷了。
而另一位唐代知名公主安樂公主,則因為喜歡各種鳥羽獸毛製作的裙子而被載入史冊。
相傳,安樂公主曾讓官署為她製作百鳥毛織成的兩件裙子,正面看一個顏色,側面看一個顏色,太陽底下一個顏色,陰影裡又一個顏色,而且有各種鳥類的形態,非常繽紛華麗。
安樂公主將其中一條裙子獻給韋后,另一條大概是自留了,這對母女不愧是引領時尚的第一夫人、第一公主。
安樂公主還用百獸的毛製作廌面,這大概是一種頭飾或者面具,韋后則收集鳥毛來製作,都呈現出鳥獸的特點,花費鉅萬之多。
安樂公主出行時,益州獻上一種單絲碧羅籠裙,縷金工藝製作了許多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卻是眼鼻觜甲都具備,遠遠便能看見。
自從安樂公主等引領時尚,開始流行起這種毛裙,貴族官員、有錢的富戶紛紛效仿,江南、嶺南一帶的奇禽異獸毛羽都被採盡了,這活脫脫是一場小動物們的災難。
而除了貴婦們奇裝異服,民間也流行胡服胡帽,女子們愛戴一種叫做步搖的釵飾,一步一搖晃,風情萬種,而且愛穿衿袖窄小的衣服,這些都不是漢族人的傳統穿戴,也被視為服妖。
這就跟今天的人,偶爾也會穿一些異域風情的衣服,是開放與獵奇的體驗。
如今一些時尚界人士,時常畫著眼燻妝、塗著烏黑的口紅,被人視為另類。
然而,這樣的裝束,在唐代也不稀奇,元和末年,流行一種圓鬟椎髻,不設鬢飾,不施朱粉,惟以烏膏注唇,狀似悲啼。
這身裝扮,仔細一看,不過就是今天的“丸子頭”、黑色唇膏,在古代被“歧視”也屬正常,畢竟,連今天的許多長輩都看不慣這樣的打扮呢!
女性愛美,男性同樣有一顆不甘平凡的心。
乾符年間,有內臣刻了木象頭塞在幞子裡,有點類似給帽子墊填充物的意思,百官見了紛紛效仿,一時之間,工匠們都忙不過來,弄了一堆砍下來的木頭塊,說這是尚書頭,這是將軍頭,這是軍容頭。
還怪有意思的!
更搞笑的是,唐昭宗時期,十六宅諸王都崇尚奢侈,各自府裡有自己的巾幘制度,其他想要效仿的人,經常就會跟人說:“為我作某某王的頭。”
當時就有人覺得,這樣的話很不吉利。
其實,古人講話也不知變通,今天的人就聰明多了,想要模仿某個明星的髮型,直接來一句某某同款,輕而易舉的事情,難道還真說要肖戰的頭?王一博的頭?肯定稱呼肖戰同款,王一博同款啊!
一句稱呼,不會是國家興衰之徵兆,只是後人牽強附會,強行解釋。
要說真正作妖服妖的男人,明朝的大人們才是,限於篇幅,男人們的戲碼下回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