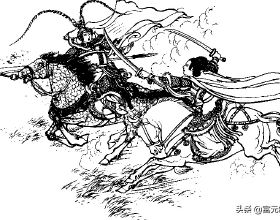在歐洲的主要國家裡,德國是相對後起的一個。起初,“德意志”更多是地理與民族概念,而非國家概念。選帝侯之間各自為政,常年處於分裂的狀態,嚴重拖累了近代化的程序。不同於英法先有政治革命、工業革命後有教育改革,德國反其道而行之,基於自身落後的國情,走上了教育立國的道路,最終實現了後來居上。那麼,近代德國的教育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發達的呢?
慕尼黑大學,1900年
宗教改革與教育世俗化
在中世紀,教育與受教育權是由天主教會所壟斷,神父與主教們幾乎是當時唯一的文化階層。天主教會為了培養神學人才,開創了“大學”這一高等教育模式。然而教會本身卻愈發腐敗,教皇利奧十世就說:“既然天主安排我們享受,就讓我們盡情享受一下吧!”文藝復興以來,人文主義的傳播,導致各個領域對教會權威的反抗此起彼伏,在大學中,也孕育著分離的力量。
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恰恰是天主教會盤剝的重災區,“贖罪券”引發了當地社會各階層的憤怒。公元1517年10月31日,維騰堡大學教授馬丁·路德公開抵制贖罪券,發表《九十五條論綱》,掀開了宗教改革的序幕。
馬丁·路德公開抵制贖罪券,發表《九十五條論綱》
馬丁·路德以“因信稱義”為起點,反對天主教會對教育的壟斷。他認為教育不僅是為了培養神學人才,也應該滿足世俗國家的需要:“即使沒有靈魂,沒有天國和地獄,只有世俗的事物需要考慮,也必須設立良好完備的學校,以培養長於治國的男子和善於理家的女子。”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他主張國家應該抓住教育權,而國民也應該義務接受教育:“我們的統治者更應該要求把孩子送進學校,這不是要把孩子從其父母手中奪走,只是為了他們和我們大家的利益才讓他們在能得到充分支援的地方接受教育。”
儘管當時的德意志沒有足夠的條件去實現路德的主張,但宗教改革的精神已然深入人心,有相當的諸侯公開支援改教,路德也被譽為“近代西方國民教育和普及義務教育運動的理論先驅”。
民族危機與義務教育體系的建立
但宗教改革也帶來了宗教戰爭,三十年的內戰給德意志造成了巨大的倒退,與西歐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形成了鮮明反差。嚴重的落後,激發了民族主義情感,激發了統治者對義務教育的重視。因為國家的發展需要各個領域的人才為之服務,國家鞏固政權也需要透過向國民灌輸主流的意識形態,教育顯然是這一過程的核心。
此時的德意志內逐漸興起了一個信奉路德宗教義的國家,即普魯士。首位國王,“士兵王”腓特烈一世於1717年頒佈了《義務教育法》,規定父母必須送其4—12歲的子女入學,學習宗教、閱讀、書寫、計算及“一切足以增進他們的幸福與福利”的課程,違者嚴懲。
1717 年,腓特烈·威廉一世頒佈法令,要求普魯士全國實施小學階段義務教育,前後共興建學校達到 1800 所之多,實現他不願見的“青年們生長在背棄信仰和無知識的黑暗之中,並將走向現世的和來世的苦難”
“大王”腓特烈二世繼位後,恰逢啟蒙運動風靡整個歐洲,而啟蒙思想家們的主張也部分為開明的君主採納。腓特烈二世正是開明君主的代表,1763年他頒佈《普通學校規程》,延續並深入了其父的教育政策:強迫教育應自5歲始,至13歲或14歲止。對不送兒童上學的家長實行罰款,並將罰款作為學校的基金。家境貧寒而無力繳納學費者可向地方行政官、資助人或牧師和宗教法庭申請津貼。第三代國王腓特烈·威廉更是將教育權牢牢掌控在國家的手中,未經許可禁止任何人私自辦學。
廣泛開展教育的第三代國王腓特烈·威廉
但此時的普魯士在發展程度上終究嚴重落後於英法。在1806年的耶拿戰役中普魯士一敗塗地,無法與經歷了大革命洗禮的法軍相抗衡,被迫簽署喪權辱國的《提爾西特和約》。這份和約再次激發了普魯士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哲學家費希特發表了《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大聲疾呼道:“惟有教育才能拯救我們擺脫壓迫我們的一切災難。”他相信,透過教育,一切財政部門都無須很多努力,就會在短時間內獲得任何時代都還不曾見過的繁榮,如果國家想要計算,如果它到那時大概也還要附帶了解各種事物真正的根本價值,它的第一筆費用就會獲得千倍的利息。
四分五裂的德意志中的普魯士
哲學家費希特發表了《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
費希特的呼籲很快獲得了國王威廉三世的積極回應。1809年3月,語言學家威廉·馮·洪堡被任命為內政部文化及教育司司長,著手負責教育改革。洪堡以“全面教育”為理念,廢除貴族對教育的特權、實行普遍的義務教育,他既認為是國民的義務:“每一個人,即使是最窮的人,也要獲得通識的人的教育。”也認為是國家的義務:“所有的學校,不是一個地方的學校,而是整個國家的學校,只能以通識的人的教育為目的。”
不想上學就得打屁股
洪堡還為普魯士設計了一套較為完整的教育體系——小學、中學、大學。小學旨在學習常識,培養能力;中學旨在學習知識,掌握學習的能力;大學則是以學習的方式參與到科研中,達到“教學與科研相統一”。尤其是高等教育,1810年,洪堡創辦了第一所現代性質的大學——柏林大學。洪堡的願景是:“在大學中,人們能夠依靠自己,從自我內在出發,理解最純粹的科學。從最基本的理解出發,自由對這一自主行為是有用的,寂寞是有益的,以這兩點為基礎,形成了大學的外部組織。”讓大學成為真正面向全社會、成為一個真正自由研究的場所。
今天柏林大學的洪堡雕像 來源.Pexels
在基礎教育階段,普魯士同樣在大刀闊斧地改革。儘管推行基礎教育已歷三代,但由於師資力量的薄弱,導致真實狀況非常糟糕。在勃蘭登堡地區,鄉村沒有固定的學校,缺乏職業教師,教學的內容仍然多是宗教教義。針對這一亂象,教育部長阿爾滕斯泰因對教師資格做了嚴格限制,將過去兼任教師的工匠與退伍軍人排除出去,並從1826年起,對教師進行教學考試。為了振興基礎教育,普魯士還積極向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齊“取經”。早在1808年,普魯士就派出由17名年輕教師組成的團隊前往瑞士學習,三年之後負責各個地區的改革工作,建立師範學校,培養了大批專業的小學教師。
伴隨著教育改革的深入,工業革命的浪潮也從英國傳入普魯士。生產力的進步,為政府保障教育入學率提供了物質基礎。從1833年起,小學的學費逐漸被免除,改善了窮苦人家上不起學的難題。1839年,普魯士又頒佈《工廠礦山條例》,開始禁止童工並讓他們接受教育。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普魯士義務教育體系最終建立起來。據統計,到1846年,普魯士各類小學達到24044所,學生243.3萬人,入學率高達82%,是世界上最早普及義務教育的國家。普魯士教育改革為工業化提供了無數的科研與技術人才,實現了國力的騰飛。1870年,普魯士在實現國家統一的關鍵——在色當戰役俘虜法皇拿破崙三世,報了當年的一箭之仇,戰後普軍元帥老毛奇不無自豪地說:“普魯士的勝局是在小學教師的講臺上決定的。”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普魯士義務教育體系最終造福了這些兒童
德國統一與職業教育的發展
統一後的德國很快將普魯士的成功經驗推廣到全國。除了原有的義務教育體系,為了順應工業化的需要,教育結構也發生了變化,職業教育愈發受到重視。
首先是文科中學不再擁有升入大學的唯一資格,面向自然科學和實用知識的實科中學獲得了同等的地位。1900年,德皇威廉二世批准《基爾法令》,承認實科中學畢業生同樣有升入大學的資格。在工業化的浪潮下,文科生的比重明顯下滑,1900年還能佔60%,到了1918年銳減到39%,而實科中學成為了新興資產階級子弟們熱衷的場所。
高等教育也隨之受到衝擊,教學與科研、生產之間實現了緊密結合,商業、技術等高等學校相繼出現。到1918年,在德國的54所大學中,有工科大學10所,農林獸醫大學9所,商科大學5所。
德國主要大學分佈
同時,中等技術學校和職業學校也興盛起來。涵蓋了建築、機器製造、採礦、食品加工等多種工業部門的技術學校與商業學校,僅1831年普魯士內就新建職業學校26所。德國統一後,到1910年,來自中等技術學校的學生多達135.6萬人。
德國還根據自身傳統,發展出了特色職業教育體制——“雙元制”。所謂雙元制,是讓青少年在企業接受職業培訓之外,又要接受職業學校的義務教育。“雙元制”由傳統的行會學徒制過渡而來,在工業化的浪潮下,學徒制已無法順應時代,工人需要進行繼續教育。在1849、1869年,普魯士兩度出臺《工商條例》,規定了學徒有接受繼續教育的義務,而僱主與師傅須免除學徒的工作量。
曾經建立在人身依附上的學徒制被廢除,轉而接受職業教育
德國統一後,凱施恩斯特首次提出把舊式進修學校轉變為按照專業劃分、以職業為導向的義務職業進修學校,並於1906年率先在慕尼黑辦學。這種改革為其他地區效法,並得到了國家的認可。1938年,職業教育最終被規定為義務教育。第三帝國崩潰後,義務職業教育為聯邦德國所繼承,1969年8月14日聯邦政府出臺《職業教育法》,現代的雙元制正式確立,成為德國經濟騰飛的一大動力。
綜上,德國近代教育體系的發展,全程離不開國家的大力支援,發達的教育也幫助德國順利搭上了工業化這列快車,並且趕超了英法這些老牌國家。德國的歷史經驗也證明了,後起國家透過普及教育來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是非常合宜的道路。
Humanitas ∣ 兩漢 晚清民國 希臘羅馬的古典時代愛好者
參考資料: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費希特;外國教育發展史料選粹.夏之蓮;外國教育通史.滕大春;近代德國普及教育之路.賀國慶;威廉·洪堡的“全面教育”理念:目標、制度與知識觀.王世嶽 陳洪捷;近代德國工業化過程中教育事業的發展.邢來順;近代德國教育改革述評.楚漢;普魯士王國義務教育政策研究(1713-1871). 武珂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