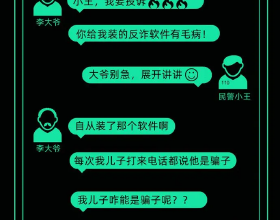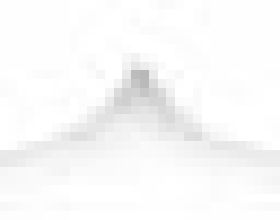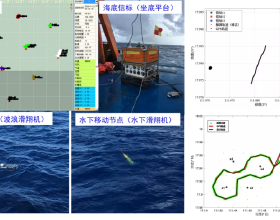村中,遠處,老婦,兩眼無神的呆坐在輪椅上。是流年凌亂了髮髻,似歲月空洞了神眸。曾經是她丈夫坐過的輪椅,也曾經是她推過的輪椅。後來,他走了,她坐上了。
回憶的最深處,約莫能回溯至二十個年頭。老婦屋前就是村道,九八年建的水泥村道至今依然堅挺,而後那些新建的水泥路卻早已粉骨碎身了。 話說她家門前剛好有個減速溝,每逢下雨便會積水。小時候和小夥伴一起,穿著長筒水靴猛踏積水,半泥半水的濺得一身!在家門口織蓆的老婦啊,照例誨人不倦,但隔天要是碰上小孩的父母,她絕不會背地裡談此種種。正如她從不參與村中八卦,安安份份的在家門口編織著草蓆,等待著在菜園裡除草的丈夫日落而歸,給人一份自給自足的安詳!
而大多村婦,喜聚於榕樹之下,齊集於屋房之中,邊用心編織邊逞口舌之快,點評上下三村,林林種種的雞毛蒜皮或倫理生死,事無鉅細,萬物皆盤!時而嘻哈大笑,時而低聲竊語。時而喜上眉梢,時而神色嚴峻。時而熙熙攘攘,時而鴉雀無聲……
話說那頭,丈夫在水圳旁簡單清洗一下身上的泥土,鏟子熟練的往肩上一搭,右手拎著兩把青菜,便踏著夕陽的餘暉歸家而去了。細長的田埂,兩邊許多不知名的雜草,中間早已寸草不生。他身後的這片泥土,是否承載了他生活的全部?是,也不是。遠遠看去,目之所及,不知有多少和他一樣腳步匆匆的人。
不一會,已回到村邊,路過孤寡的二老大爺門口。他便抽出較大的那把青菜,放在門口的石板凳。如若碰巧二老大爺在家,便會慣例百般婉拒。反正無論過程如何,菜是給了的。小時候以為他倆是叔侄,後來才知道沒啥關係。“農村咩野都好,就係人心吾好!”是,也不是。
踏入家門,老婦已經把飯做好。他簡單侍弄炒個青菜,一肉一菜往小木桌一放,標配的一頓農家飯便開吃了。她在屋裡吃著,他卻拿個較大的雞公缽盛好滿滿的飯菜,蹲坐在門口的石板凳了。一副怡然自得的樣子,邊吃著偶爾還和路過的人扯上兩句。老婦在屋裡頭聽到了,不忘又喋喋不休地念叨著他。
後來出外念大學,又後來到其他城市工作,後知後覺已經很少回村裡。那主幹大田埂也變成了水泥路,但那片承載著他許許多多的泥土還在。有次碰到老婦幫丈夫推著輪椅,在這水泥路散步。每一步都走得很慢,很慢。或許是推得有點吃力?或許是希望時光多點停留?不得而知。兩人沒有任何的言語,她默默地走著蹣跚的步伐,他默默地看著遠處自家的菜園。我也不自覺的隨他目光的方向看去,才發現那片田地早已雜草叢生,迴歸自然,再無晚歸的腳步。
而今,老婦坐著他曾經坐過的輪椅,不同的是已經沒人推她去散步了。一群幼小的孩童打打鬧鬧路過她家門口,也不會再有誨人不倦的場景。
看著這無憂無慮的小孩童,十年後,二十年後,誰又會執筆?誰又會成為字裡行間的那個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