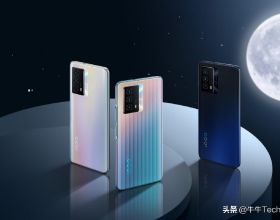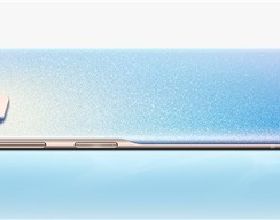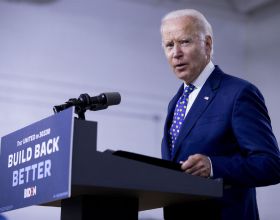鐸,一種古樂器,像一個大鈴鐺,中間有舌,銅舌者為金鐸,木舌者為木鐸。
“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與金鐸在戰場上鼓舞士氣不同,木鐸更多與行政事務相關。史書記載,夏禹治理天下,在醒目的地方置放鍾、鼓、鐸、磬以及鼗五種樂器,就五類問題分別徵求有識之士的意見和建議。其中“告寡人以事者振鐸”,就是讓有識之士擊打木鐸,告訴他政事上的不足。由此可見,那時木鐸儼然是監督的一種象徵。
木鐸的監督象徵在《尚書·夏書·胤徵》中更加明確。據記載,夏代胤侯受命征伐羲和部落,在行前動員講話中,他說,“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每年孟春之月即農曆三月,宣令官會在人群聚集之處,一邊擊打木鐸,一邊宣佈政令法規,以提醒百官注意,互相規勸,提醒百工擯棄奇技淫巧,依其技藝進行勸諫,如果令行而禁不止,國家將予以懲罰。胤侯認為,征討瀆於職守、嗜酒荒亂的羲和部落,並非不教而伐,而是“木鐸徇於路”在先,師出有名且名正言順。在這裡,木鐸進一步成為宣示政令法令、警示百官百工的象徵。
《周禮》中多次提到“木鐸”。《周禮·天官·小宰》雲:“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漢代大儒鄭玄解釋為,“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眾,使明聽也。”略有不同的是,其宣示地點不在路上,而在宮中,宣示者不是作為使臣實施宣令的“遒人”,而是協助履行監督職能的專職官員“小宰”。小宰很重要的一項工作是輔佐大宰,按照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等六種標準來評判官員。小宰擊打木鐸後,會將有關政令法令懸掛宮中,並履行監察職能,督促官員遵章守紀,盡心盡責,服從王命。《周禮·地官·鄉師》記載,“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以市朝。”這裡的宣示者也不是“遒人”,而是掌管教化履行監督地方官員之責的鄉師,宣示的內容更加明確,主要是朝廷的徵召及命令,在市集擊打木鐸,同樣是提醒大家注意,引起重視。
據《周禮》記述,木鐸還有一個特別的功能,與火禁相關。對於火禁,有人認為是為了防範火災,也有人認為是古人定期熄火、重取新火以示對火種的敬重,熄取之間,實施火禁。但將木鐸與火禁聯絡起來,無論掌管王宮戒令的宮正,還是掌管國家火禁的司烜氏,都合理而巧妙地運用了木鐸警醒、監督的象徵功能。
事實上,當時木鐸在民間還有更廣泛的運用。“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詩經》中的國風,大多是周代采詩官春天到民間搖著木鐸搖回來的。木鐸噹噹作響,歌謠字字成行。歌謠隨口而出,發自內心,是民心民情的真實反映。正是透過采詩,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以此反躬自省,查糾不足,改進政策,實現“富而教之”。
將木鐸的象徵意味推向高峰的,是《論語·八佾》中的一段記載。一個從儀這個地方來的鎮守邊界的官員,受到孔子接見後,出門對孔子的學生說,“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孔子對他究竟談了什麼,我們無從知曉,但就當時他對孔子的評價如此之高如此之準,不能不說他慧眼獨具。無論是從政魯國盡心職守,還是周遊列國顛沛流離;無論復興周禮,還是整理文獻,抑或教書育人,孔子始終像一個巨大的木鐸,一刻不停地敲擊著,以琅琅清音警醒世人,教化世人。
千百年來,寫木鐸的詩很多。蘇軾有一首詩,將木鐸的象徵意義上升到以德治國、天下歸仁的政治理想:“靄靄龍旂色,琅琅木鐸音。數行寬大詔,四海發生心。”
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正月,朝廷內宴,按例,翰林院侍臣應獻詩宮中,貼上於閣中門壁,以供品賞。蘇軾向皇帝、皇太后、太皇太后一口氣進獻了十餘首帖子詞,第一首便是這首“琅琅木鐸音”。
那年冬天,天降大雪,寒冷異常,百姓生活困難。朝廷下詔,“雪寒異於常歲,民多死者,宜加存恤,給以錢穀;若無親屬收瘞,則官為葬之。”後來又下令,“以大雪寒,賜諸軍薪炭錢;再令開封府閱坊市貧民,以錢百萬計口量老少給之。”《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太皇太后高氏特地詢問災民情況,“大雪,民間不易,已令散錢,還均濟否?”
蘇軾對朝廷洞察民情、憫恤民生、安撫民心的做法倍加讚歎,因而發出“數行寬大詔,四海發生心”的感慨。此時的蘇軾已過知天命之年,歷經坎坷後,他對民生多艱有更深的理解,對改善民生也有更多的設想。哲宗即位後,太皇太后高氏攝政,蘇軾復出官拜三品,離宰相一步之遙,當時的哲宗年僅十二歲,跟隨他讀書學習,是以蘇軾對朝廷德政更有無限的期盼。居廟堂之高,憂江湖之遠,這也許正是蘇軾將木鐸的意象與化生萬物的天地大德相連的原因所在。而這樣的意象,對木鐸問政、監督、采詩、教化等原有功能,既是承接,更是昇華。(趙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