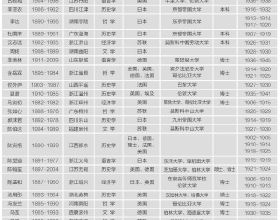“下午一點半,踏進臺兒莊西門,眼前是一幅斷牆殘垣的焦土景象!全城再也找不出完整的房屋……在寨子內,還有不少忠勇的我軍的屍首,有的雖然全身焦黑了,但仍屹立在牆角旁,左手持著手榴彈,右手持著步槍,做奮勇搏擊狀,在殉國的那一剎那,依然保持‘死而不已’的戰鬥姿態……”
這是《新華日報》記者陸詒1938年4月7日在臺兒莊戰役的前線報道。
“願盡吾輩全力拯救中國,待我中華揚眉吐氣之時,我們再相見!”
這是在黃埔軍校的同學錄裡,同學給陳建武留下的一句話。
意氣風發投身革命洪流
陳建武出生在湖南郴州的一個書香門第,家中兄弟三個,陳建武排老二。
陳建武的父親是晚清秀才,家中日子雖然過得勉勉強強,但是兄弟三人的教育一點也沒落下。“我伯父和我父親小時候都念過私塾,爺爺也比較有文化,可以說家裡讀書的風氣還是很好的。”陳建武的侄子陳秦玉說。
雖然父親接受的是儒學八股的薰陶,但是面臨中國的大變革,陳建武兄弟們有自己的想法。面對日益疲敝的國計民生,陳建武認為,革命才是拯救國家的唯一道路。
於是他在34歲那一年進入了黃埔軍校,毅然投身國民革命的大洪流中。因為從小讀過書,有較好的文化功底,陳建武進入軍校以後,成為了一名文職教官。
參軍的時候陳建武已經結婚,但是並沒有孩子。夫妻倆平日相敬如賓、感情深厚,一朝分別有很多不捨。但是民族存亡之際,陳建武的妻子也明白國大於家的道理,再多
不捨也只是默默為丈夫打點好行裝,囑咐他出門在外照顧好自己。
為見一面跋涉百里
參軍後,陳建武隨軍隊從廣東一路北上,參與了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那個年代通訊不暢,陳建武參軍以後家裡就再沒有他的音信。
“有一次我爺爺聽人說我二伯的軍隊行軍到湖南境內了,就趕緊想去見他一面。”湖南山區交通不便,道路崎嶇,陳建武的父親為了見兒子這一面,一路邊走邊打聽,徒步跋涉了近百公里路。可是陳父最終也沒有找到陳建武的具體位置,沒能見上這最後一面。
1938年陳家收到了陳建武犧牲的通知,才知道他在臺兒莊戰役中犧牲了。知道訊息以後,家裡人悲痛欲絕,“我父親跟我說,我爺爺拿著那個通知當即就掉下淚來。”
陳建武的妻子龔氏知道丈夫犧牲,一時晃了神,半晌才嚎啕大哭起來。
“日本人侵略我中華,我兒是為保衛國家,保衛四萬萬同胞犧牲的,我兒的死重如泰山!”陳建武的父親淚眼望著兒媳婦,堅定地說。
妻子為他守寡一生
陳建武無後,他犧牲後妻子卻再沒有改嫁。“我父親和我大伯父兒子多,我二伯母就把我們這些侄兒都當親兒子養。”陳秦玉記得,小的時候二伯母總是無微不至地關心自己,“小時候不管是受了委屈還是闖了禍,我都會去找二伯母,她總是很溫柔地安慰我。”
陳秦玉說,二伯母有時候會說,看到這些侄子,就像又看見了丈夫陳建武,心裡總有滿滿的溫情。
龔氏直到老年去世,也一直是一個人。她晚年的時候,國家認定了她的烈屬身份,覺得她一個人日子過得不容易,想為她申請貧困補助。
“我二伯母最後還是拒絕了。她說她有那麼多侄子都會管她,她並不是一個人,所以她不願要國家的補助。”陳秦玉說,他們兄弟都很孝順這個二伯母,老人臨終也走得很安詳。
一束鮮花寄託哀思
老一輩人的去世也帶走了二伯父安葬地的訊息。“我父親平時很少跟我們說這些,他隱約講過二伯父犧牲在哪,但是那時太小已經記不得了。”
如今陳秦玉已退休,經常回憶起二伯母對自己的關懷,也很想重新找到二伯父的安葬地。“我去我們當地的資料館也查過資料,但也是收穫甚微。”
直到今日頭條釋出了文章《湖南郴州英烈陳建武在臺兒莊戰役中犧牲,他的親人,如今在哪裡?》,陳秦玉看到後馬上了聯絡了頭條尋人的工作人員。“因為資訊有些殘缺,開始還不能確定就是我二伯。”在陳建武為數不多的個人資訊中,有明顯的一欄是:妻子龔氏。正是憑藉這個,陳秦玉最終確定了二伯的身份。
“可以想象,當年二伯在犧牲的時候,心裡一定正掛念著家裡的親人,掛念著他摯愛的妻子吧!”
陳秦玉說,如今國泰民安,祖國日益強大。等疫情好轉,他一定和家人一起去二伯的墓前獻束花,讓二伯知道,他的血沒有白流,他的理想已經實現。
緬懷先烈功績,告慰先烈英靈,傳承紅色基因,講好紅色故事;頭條尋人發起“尋找烈士後人”專案,與臺兒莊大戰紀念館合作,共同為烈士尋找親人。在以往的成功案例中,媒體接力尋找烈士後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今日頭條誠邀全國各地媒體一起參與到“尋找烈士後人媒體志願服務團 ”中來。
如有烈士後人相關線索,或希望共同參與尋找烈士後人的媒體,歡迎聯絡頭條尋人(郵箱:[email protected];電話:010-58341776、010—8343485)
如有烈士後人相關線索,歡迎聯絡頭條尋人(郵箱:[email protected];電話:010-83434440、010-83434485 ),將有專門的工作人員對資訊進行核實和後續跟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