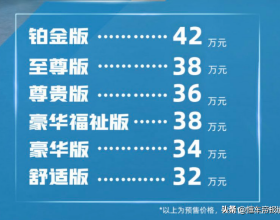“人們的生存離不開水”。這已經成為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共識,水資源是人們生產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項寶貴財富。
由於地形的差異,各地區水資源的存在狀況,不可能完全符合人們的需求。
人們為了控制水資源的合理利用,為了人為調節大自然的旱澇災害,在世界各地修建水利工程。
根據不完全調查統計,世界上大規模、長距離的調水工程已經達到160多項,遍佈24個國家和地區。
在已經建設的調水工程中,巴基斯坦的西水東調,年調水量達到148億立方米。
“世界三大調水工程”分別為中國的南水北調,美國加州的北水南調,還有前蘇聯的東水西調。
前兩項工程可以說是造福了一方百姓,為人民的生活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而前蘇聯的東水西調卻因為不恰當的舉措,造成了一場難以轉圜的自然災害,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中國的南水北調,造福一方人民
中國“南水北調”的構想始於1952年,新中國建設以來,這是政府投資最大、涉及面積最廣的一項工程建設,南水北調關乎到中國人民的長遠發展。
這項偉大的工程一旦竣工,就可以解決北方城市嚴重缺水的問題,從而提高國內水資源的分配效率。
北方城市的發展受到水資源緊缺的限制,京杭運河從濟寧到徐州段,因為缺水面臨著斷流的危險。
南水北調工程徹底解決了這一個弊病,魯北和蘇北兩個地區的糧倉基地,因為得到了豐富的水資源而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當時關於“南水北調”,在全國上下都掀起廣泛的爭議,有人說:“這樣簡單粗暴的調水工程很可能汙染水資源,到時候人們都沒有水用,反而得不償失。”
還有人提出:“這樣做可能會破壞長江的生態環境,影響那裡的居民生活。”
在此期間,有無數水利專家被安排到長江地區調查,國家以謹慎的態度,認真分析這一工程的可行性。
可以說南水北調工作的開展,集結了全中國的物力人力。
中共黨史出版社發表的一本書,名叫《南水北調回顧與思考》。
書中記錄了南水北調辦主任張基堯,主持這項工程時,目之所及的方方面面。
這本書以他個人的眼光,見證了那段偉大的歷史。
“回顧我一生從事的水利建設的歷程,其中最難忘的要數2003-2010年的南水北調工程。”
張基堯在書中所寫下的這句話,為我們揭開了歷史的面紗。
1998年,長江地區暴發了特大汛情,國家和軍隊為了搶救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國家決定以後不但要加強雨季的防控建設,還應該利用好長江地區的洪水資源,如果能將這些多餘的水輸送到北方去,可以極大地緩解北方乾旱的情況。
一想到這裡,南水北調工程就緊鑼密鼓地投入到規劃之中。
2000年華北地區遭遇了嚴重的乾旱情況,張基堯曾經陪同溫家寶總理到山東地區察看災民的情況。
那時山東的旱區已經發展到人們難以預測的程度,曾經水草豐沛的南四湖地區,現在早就乾涸見底。
停泊在湖中的漁船,被火紅的太陽曬得乾裂,水裡的魚蝦早就消失了蹤影。
曾經富饒的膠東半島變成一片荒蕪的景象,水庫裡的存水量都被大功率的抽水機給抽乾了,煙臺、青島等城市地區開始實行限時供水的政策。
很多大宗的國際訂單也因為旱災的影響被迫推遲,山東地區的經濟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
溫家寶總理乘著列車來到這片乾旱的土地上,他和山東地區的人民一起感受炙熱的蒸汽撲面而來。
他神色凝重、一言不發,各級領導幹部們焦灼的心情不知道該如何化解。
2000年的旱情像是一針催化劑,極大地促進了南水北調工程在全國範圍內的實施。
專家們加緊進行前期的調研工作,黨中央領導小組用很短的時間統一各方面的意見,為加快決策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建設神定河汙水處理廠是“南水北調”工程的第一批開工計劃,神定河是湖北地區匯入丹江口水庫的重要連線點。
那裡長期缺乏處理汙水的配套設施和管理體系,因此有大量的工業廢水源源不斷地流淌到清澈的河水中去。
張基堯接受了這個艱鉅的任務,當他第一次到達神定河附近進行調研的時候,他看見醬黑色的河水散發出一陣刺鼻的臭氣,周圍的居民早就對這條“臭河溝”有意見了。
他們知道張基堯是從北京派過來的領導,一見到他出現在神定河邊,就紛紛上前去把他圍住。
居民們指著神定河裡面的黑水說道:“你看看這河,臭水都流到水庫裡,將來的人都得喝中毒。”
張基堯見到老鄉們一張張憂愁的臉,他們希望政府能夠快點解決用水問題。
那些殷切的目光讓張基堯感到很大壓力,他透過實地考察,切實瞭解到這裡的情況,認為建設汙水處理廠是一件勢在必行的事情。
儘快落實行動,不僅關係到庫區周圍居民的利益,還關乎“南水北調”工程的長遠發展,他回了北京,立即寫了一封建議書,推進神定河汙水處理廠早日投產。
可是處理廠在建設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多現實問題,當地政府的財政資金緊張,如何保證耗資巨大的工程正常運營成了一個難題。
丹江水庫地區多是山川丘陵地貌,這樣的地形導致交通欠發達,當地的經濟發展受到嚴重阻礙,建設汙水處理廠讓當地政府和居民承載著前所未有的壓力。
經過中央政府的財政撥款支援,丹江水庫基本解決了財政資金短缺的問題。
轉眼間就到了2009年,神定河水的汙染程度得到了明顯的緩解,曾經散發臭氣的黑水變成清澈的河流,河水兩岸長出了碧綠的青草,原來可是寸草不生的。
汙水處理廠的執行效率也達到了80%以上,處理後的泥土還能讓科研人員改造成能夠利用的肥料。
建設水庫需要組織大量的村民轉移居住地點,而淅川縣是丹江口水庫地區需要轉移的重點縣,河南省的16.4萬移民大多集中在淅川。那裡是河南省境內的貧困縣。
2009年6月,張基堯帶領隊員們到淅川去考察情況,可是縣委書記給出了一個模稜兩可的答覆。
他說道:“建水庫要轉移村民,這次任務要按時完成,地方工作人員要面臨很大的壓力。”
張基堯見縣委書記一味地強調時間緊、任務重,但也沒有說出具體原因,他語重心長地詢問道:“你要告訴我,困難到底出現在哪裡,你需要什麼樣的支援,我們會盡量幫助你。”
當晚他和縣裡的工作人員徹夜交談,提升他們按時完成任務的信心。
最終的實踐證明,只要肯下功夫,淅川地區的移民沒有拖後腿,他們按時完成了黨和國家交給的任務,也促使“南水北調”工程如期完工。
截止到2021年,中國南水北調的東線和中線工程,累積調水量達到494億立方米,通水的7年以來,北方地區受益的人民累計達到1.7億。
40個大中型城市的經濟發展格局得到了明顯最佳化,有效促進了全國政治經濟的健康發展。
加州北水南調,促進農業發展
加利福尼亞地區的氣候有著相當優厚的條件,這裡十分適宜人類居住,唯一的缺點便是水資源分配嚴重不均。
加州北部的雨水量十分豐富,夏雨充沛的時候甚至會造成洪災,而南方地區降水量少,人們經常因為缺水而愁眉不展。
加州南方地區的光熱條件充足,有2/3的人口聚集在南部生活,這與當地水資源的儲存量正好成反比。
加利福尼亞的地形崎嶇不平,中部地區的谷底土壤肥沃,南方地區的經濟發展受到了自然環境的嚴重製約。
上世紀30年代開始,羅斯福新政時期,這位總統就將目光聚焦於加州地區的跨流域調水工程,專家們先後到該地區進行詳細的調研取樣,最終規劃出“北水南調”的具體路線。
1950年,加州政府開始全盤落實關於“北水南調”的工程建設,要找到解決南北兩地旱澇問題的兩全之策。
當地的居民對此次行動的意見不統一,1956年加州北部再次發生了大面積的水災,使得居民們基本確定了態度,他們認為:“北水南調不僅對南方同胞有利,也符合自身的長遠發展”。
在1960年,政府舉行的加州公民公決中,有580萬人參與投票,北水南調的計劃以51%贊同的微弱優勢順利透過。
1973年,加州調水工程的主體建設基本完工,1990年才完全達到預期的輸水能力。工程資金則由發行債券等方式籌集,不用當地政府撥款。
總而言之,這是一個耗時耗力的大專案,根據政府的不完全統計,此次南北兩側的輸水線路總長度達到900多千米,調水線路總長達到1151米。
這次工程的調水量在52億立方米左右,給加州南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轉機。
北水南調之後,加州南部得到了長足的滋養,從前乾旱的土地上也可以種植甜美的葡萄,農民依靠發達的機械化種植技術,迅速將南方的農業發展起來。
雖然水庫建設截取了原來流向舊金山灣區的大量水源,造成當地的水質變差,以及一系列後續問題,但整體來說還是利大於弊。
蘇聯東水西調,鹹海瀕臨消失
前蘇聯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整體面積達到2240萬平方千米,大約佔世界陸地面積的1/6。
蘇聯地區的緯度高氣溫低,中亞地區是最溫暖的一塊區域,對於苦寒的蘇聯來說,如何利用好這些地區,發展農業生產,成為一件十分緊迫的事情。
上世紀50年代,蘇聯政府決定擷取阿姆度河以及謝爾河的水利資源,用來促進中亞地區的發展農業,這些水流原本會流入鹹海。
1967年東水西調工程正式竣工,這一專案在一開始確實獲得了很大的成效,中亞地區接收到源源不斷的水流,為農業種植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條件。
中東地區一躍成為世界棉花出口最大的地區,極大地帶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
但是問題很快就暴露出來,流入鹹海的水源逐年減少,那裡的漁民靠捕魚維持生計,至少有4萬人在這片水域生活。
1947年蘇聯軍艦都可以進入鹹海同行,然後東水西調加速了當地生態環境的惡化,鹹海的水域面積也在逐年萎縮。
2004年的時候,鹹海面積已經萎縮到原來的1/4,再加上中亞乾燥的自然環境,形成了難以挽回的惡性迴圈。
鹹海原本是世界上第四大湖泊,經此變故,湖水的鹹度急劇上漲,當地的捕魚業也銷聲匿跡。
東水西調工程被迫停止,中亞經歷了短暫的繁榮消失之後,將要面對的是滿目瘡痍的大自然。
目前處於鹹海地區的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已經派了官方專家們,絞盡腦汁地想要緩解該地區的惡劣條件,這場人為闖下的災禍,到底該如何收場?
前蘇聯的教訓告訴人們,人們在改造大自然的時候,一定要謹記一條原則,就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人們要對大自然保持敬畏的心態,切記不要做出超出人類能力範圍內的改變。
當前人類急需解決的是“全球變暖”問題,而我國一直以來,都以負責任的大國形象,致力於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2020年中國在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中公開發表了我們的態度:“中國將用更加有力的措施,爭取在2030年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
這是中國給全世界人民的莊嚴承諾,要解決世界範圍內的環境問題,需要發達國家作出更大貢獻,期盼全世界人民能儘快聯合起來,共同打造人類的美好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