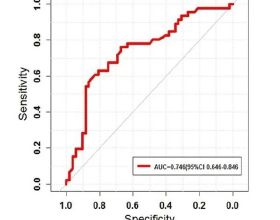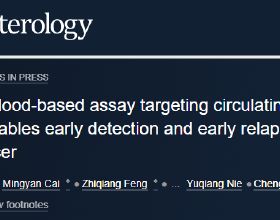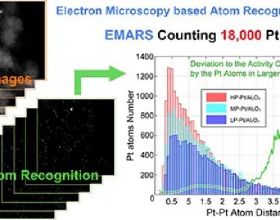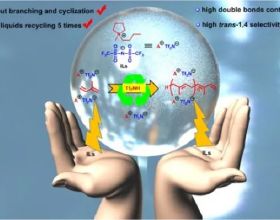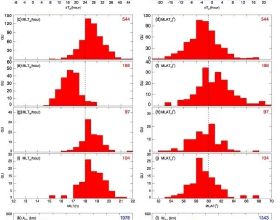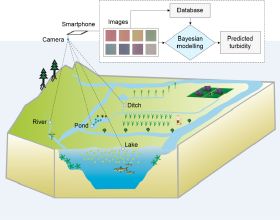“臘月風和意已春,時因散策過吾鄰”,是陸游《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一詩裡的起句,寫的是詩人臘八日外出時的見聞。臘八日,詩人拄杖出門散步,感覺到風裡的一絲和暖,病後出門,路過鄰居家,覺得分外親切,如沐暖風。再往遠處走一點,但見柴門裡的草煙漠漠,野水之濱的牛跡重重,一切所遇皆欣然,皆有節物時新的一番春意。
臘月過了,便是春天。立春以後,春風更暖和了。“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是王安石《元日》詩中的句子,寫的是正月一日飲屠蘇酒的習俗。這種習俗在南朝梁·宗懍的《荊楚歲時記》中也有記載:“正月一日……於是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屠蘇酒、膠牙餳”,過年時,大家互相拜年,一起喝酒、吃糖,多喜慶熱鬧啊。詩文中所提到的屠蘇是酒,春風也是酒,都能醉人。酒自醉人,而人在春風中會自醉,醉人的方式不同,一是被動,一是主動,但醉意卻是相彷彿的。人能有醉,何其幸也。
因酒而醉,或是醉在春風裡,都是件幸福的事。我總覺得春風醉人,是難以自知自覺的,卻分明又是可以隨時感知的。醉而難覺,醉而自知,真的很矛盾。有時候,我覺得春風更像是一位藝術家,她讓一部分人能感知她的種種好,卻讓另一部分人雖沐春風,卻難知春意。春風,愛逗趣兒,是有些調皮可愛的。伊瑟爾說,文學語言包含許多意義未定性和意義空白,“作品的未定性和意義空白促使讀者去尋找作品的意義,從而賦予他參與作品意義構成的權利”。很多時候,我覺得春風也有文學語言的某些特質,春風吹拂的萬物,便是她的作品,我們被春風吹拂,也會參與春風的創作,去感受、感知春風尚未確定的某些意義。如此,你我皆在春風裡,皆可為春風,春風便是可親近的了。
我想用春風做一把豎琴,以天地為弓,萬物當弦,共奏春之曲,共同填寫春風意義未定性和意義空白。大概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春風的深情和深意。在春風拂過的琴絃裡,喧鬧有聲,也容易被我們發現的,是群山起伏的長調、河流蜿蜒的低迴、城市和村莊的片刻停頓、一片森林的共鳴、一棵樹輕輕的顫動、一根柳絲低低的耳語,還有芽和葉、花和蕾的密語、樹液和蟄蟲悄悄交流的聲音,也許還有林中清澈的鳥鳴和村莊裡的雞鳴犬吠,還有許多我們無法捕捉,也難以想象的聲音,這些聲音的和鳴,與春風有關,與一把想象中的豎琴有關。如果沒有用春風做成的這把豎琴,春天該是安靜而又寂寞的,那麼欣然春意和繽紛色彩,又有多大的意義呢。
用春風做一把豎琴,山便是它的琴絃。風撥動南山和北山的草木,發出不同的聲響,帶來不同的訊息,南山的草木已經萌發,北山的冰雪還在消融,在冷與暖之間,在琴絃之上顫動的春風,也在撫平山與山之間的界線。
在春風裡,一條河流婉轉地訴說著自己的心事。春水初生,有許多心事漸漸豐滿起來,有了傾訴的慾望,她能說給誰聽呢,誰又有耐心站在水畔聽她們瑣碎的心事呢。一陣風來,帶走了她們的低語,或是喧譁,那是紛繁的春水的心事。
一座城市蔓延開來,面積可能很大;而一座村莊,像是被城市遺忘的一些碎片,散落在城市的周圍,散落在山水之間。風在城市裡也許會迷路,而村莊裡的風要自信得多。在城市裡,聽風亂語,像是撥錯了琴絃,彈錯了調子。在村莊裡,春風與萬物和鳴,一切都現出盎然生機。一棵樹在風中,也學會了抑揚頓挫,俯仰搖擺。
在春風裡,遇見一根柳絲,你會堅信它就是豎琴的某一根弦。柳絲上吐出的芽葉,淺黃淡綠,是掛在琴絃上的一串串音符,隨時等待被春風奏響,如果音符也有顏色,它肯定是早春柳芽和各種植物的欣欣向榮的顏色,繽紛而又熱鬧,像是一曲合奏。路邊,一根剛露出地面的小草,也在努力長成春風豎琴的弦,等待著參與春風的交響。春風與萬物,本來就是一把豎琴。
圖片源於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