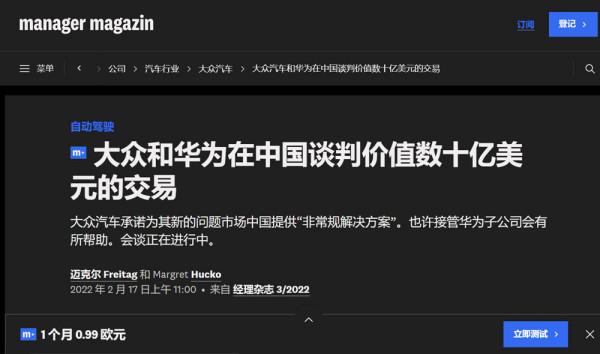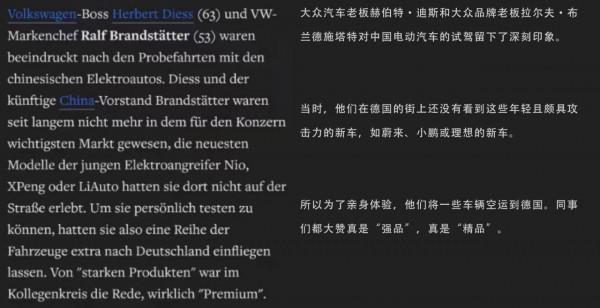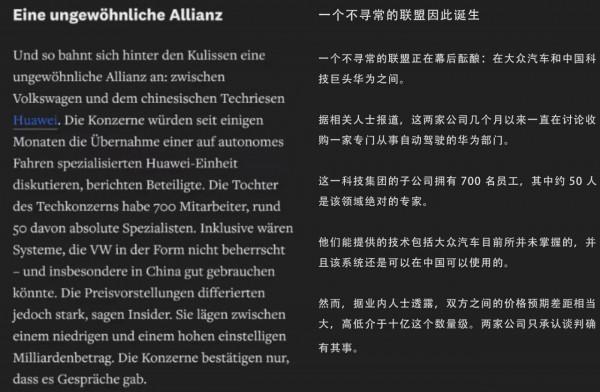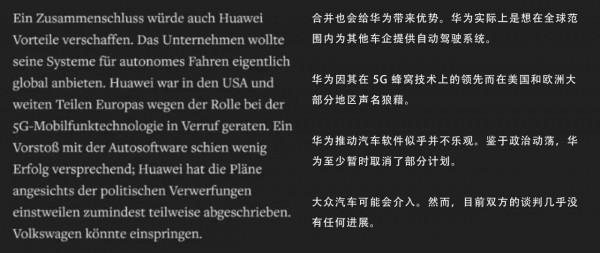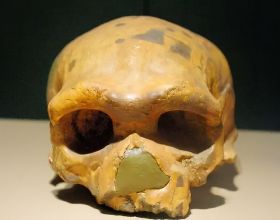“那麼,任正非這次又因何要將華為的部分業務擺上談判桌?而與華為傳出“緋聞”的一方為什麼又是大眾,不是豐田不是戴姆勒?為什麼這條訊息又恰恰在德國總統大選剛剛結束就被爆了出來?”
當捕風捉影的流量熱度逐漸消退之後,也是時候翻開另外一面窺探深層格局。
柏林時間2022年2月17日上午11點,一個名為MichaelFreitag的博主在德國《經理人雜誌》上釋出了一則短訊息,標題叫做:
“大眾集團和華為公司正在中國和華為公司談判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交易。”
該訊息一經爆出就迅速被路透社等海外知名媒體轉載,國內各大網站也充斥著“大眾集團將要收購華為自動駕駛部門”的相關報道,幾乎已經將雙方的交易描繪成板上釘釘的事實。
引得外界猜測的主要依據在於訊息中有提到,大眾汽車正在為中國市場的問題尋找“非常規解決方案”,並且稱“也許收購華為的子公司會對此有所幫助,會議正在洽談中。”
弔詭的是,比起通篇猜測雙方可能的合作形式,卻鮮有人去進一步求證訊息的真實度。再加上德國《經理人雜誌》又是一個只有會員才能全篇瀏覽的付費平臺,因此究竟有多少內容是被誇大演繹的也無從得知。
不過很湊巧,筆者在知乎上認識的一名網友恰好在德國留學,在他的幫助下也終於有機會能看清事件的全貌。
這一事件還要從大眾的兩位CEO說起。赫伯特·迪斯和拉爾夫·布蘭德施塔特有一次試駕了“蔚小理”三家的新車,並且整個過程令他們感覺很“哇塞”,於是便空運了幾輛送回德國打算讓他們的同事也體驗一下。
但是經過大眾方面的討論得出,他們認為捲入到中美兩國貿易爭端的風險太大,於是就策劃了一個“不同尋常的聯盟”——最近幾個月一直在和華為商討想要收購一個自動駕駛業務部門的事,而這個部門擁有700名員工,其中50個人是絕對的專家。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儘管華為整車BU自成立以來內部結構便不斷調整,但是整個負責自動駕駛業務的部門卻不可能只有700人。早在去年四月,時任華為整車BU總裁的王軍就曾指出,華為的自動駕駛團隊將在本年度擴充至2000餘人。
因此,真正擺上談判桌的並不是所謂的什麼 “子公司”,也不是華為的整個自動駕駛團隊,而應該是在整車BU擴充之後,衍生出來的某個二級或者三級部門。
然而根據現有的訊息來看,目前這一合作並未有更深層次的進展,一方面是由於“雙方相互之間的信任感不大”,而另一方面則是大眾方面給出的價格和華為的要價相差了數十億美元。
由曾記得在20世紀初,任正非在內憂外患的局面下打算將華為的部分業務出售給摩托羅拉。
彼時,華為因錯失小靈通增長熱潮,被UT斯達康技壓一籌;天才少年李一男帶資出走,另立山頭和華為對著幹……而任正非也因為積勞成疾患上了抑鬱症,甚至還剛剛經歷了母親的過世。
如此混沌的局面才讓任正非動了斷臂求生的心思,而眼下華為的境遇和當年相比卻要好上太多。
那麼,任正非這次又因何要將華為的部分業務擺上談判桌?而與華為傳出“緋聞”的一方為什麼又是大眾,不是豐田不是戴姆勒?為什麼這條訊息又恰恰在德國總統大選剛剛結束就被爆了出來?
或許,訊息中明確雙方利益得失的部分是解答諸多疑問的關鍵要素。
“收購的華為團隊能為大眾提供某些尚未掌握的技術,並且以大眾目前的情況來看還無法將這種技術應用在中國市場;華為有意向全球市場推廣自動駕駛技術,但是由於其領先的5G技術難以在美國和歐洲市場獲得認同,但是如果借大眾的手就可以辦到。”
其一是大眾收購華為的自動駕駛部門,將會加速其在中國本土的智慧化程序。大眾集團CEO赫伯特·迪斯早就勵志要在2025年以前超越特斯拉,成為全球電動汽車市場的領導者。中國市場自然是最為關鍵的發力點之一。
而大眾目前在中國市場的銷量卻不盡如人意,不光是在整體銷量上的嚴重下滑,被大眾寄予厚望的ID.系列也未能實現年初設定下的目標。儘管ID.系列在歐洲市場能夠和特斯拉掰掰手腕,但是在智慧化尤其是自動駕駛技術上卻無法滿足中國消費者的需求。
一方面是在市場環境的培養下,中國消費者在智慧座艙、智慧駕駛等新新概念上的接受程度更高;而另一方面則是中國的交通狀況相比歐洲要複雜得多,因此相比海外品牌,本土品牌則更能夠理解消費者的心理,家門口的優勢也讓其在自動駕駛技術上的發力更加容易。
眼下,華為在這方面領域早就擁有一套成熟的體系,由MDC智慧駕駛計算平臺、ADS智慧駕駛系統,再到鐳射雷達等感測器組成的模組化方案,可供其他車企直接遷移。
其二是華為僅需通過出售部分駕駛團隊,就可以順勢深入歐洲汽車市場。儘管在主觀意願上華為或許並不情願這樣做,意味著就要在某種程度上和大眾共享自己在自動駕駛領域的超過三萬餘件專利,但是這樣對於華為來說依然是穩賺不賠。
華為眼下的面臨的困局人盡皆知,短短三年的時間裡華為被美國製裁了四次,在手機領域的市佔率也從原先的全球第三下滑到了如今的全國第六,2021年的營收相較2020年也下滑了接近三分之一。出售部分自動駕駛部門或許可以換回些許現金流,不過卻仍然是杯水車薪。
之所以華為願意和大眾坐上談判桌,正是因為訊息中所述的“可以讓華為借大眾之手開啟歐洲市場”。當華為目前仍然無法在短時間內消弭外國制裁所帶來的影響,或許只有繼續拓寬汽車市場才能夠讓華為看到翻身的希望。
相比由出售部分自動駕駛部門換來的數十億美元,更能令任正非心動的則是以供應商的身份和海外知名車企達成深度契合,並且以此為跳板來展望整個歐洲汽車市場的星辰大海。
時至今日,又不得不把任正非簽署的那份“華為不造車,但我們聚焦ICT技術,幫助車企造好車”的內部檔案再拿出來好好審視一番。任正非奉行的長期主義每每都能夠讓華為像顆溜光的石頭一樣,即便是撞上硬邦邦的鐵板也能在轉個彎兒的功夫就擺脫被動的局面,將外界強加給自己的壓力再通通如數奉還。
任正非雖然不讓華為下場造車,卻給華為的汽車業務創造出進軍歐洲市場,乃至未來拓寬至全球市場的無限遐想。
此外,這一事件亦可以站在更為宏觀的視角進行解讀,其所帶來的影響力遠遠不只侷限於這兩家企業本身。
就在數日以前,德國總統的換屆選舉剛剛落下帷幕。作為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的老搭檔——施泰因邁爾將作為第十三任德國總理正式履新,不僅成為自1994年以來首位獲得連任的德國總統,同時也讓在默克爾卸任總理之後,困擾德國汽車工業許久的領導問題也落下帷幕。
默克爾對於德國汽車工業的貢獻不言而喻。默克爾自上任以後,還曾經大力推進德國與中國在汽車工業之間的相互交流,在她任職期間曾經先後十二次造訪中國,並且還簽訂了一系列有助於雙方汽車工業發展的合作協議。
有意思的是,歐洲媒體還將默克爾比作是“大眾汽車守護者”,在其訪華的所有日程安排當中,只要涉及到兩國經濟貿易的合作談判,那麼隨行者之中就必然會有大眾汽車的CEO。
此外,默克爾還執著於德國汽車工業向新能源汽車的轉型。2019年,默克爾硬是將本應在2020年結束的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延續到2025年底;默克爾還宣佈德國將在2030年前建造5萬個公共充電樁和100萬個私人充電樁。
“我的任務就是要確保德國汽車工業平穩轉型”,默克爾在總結自己的產業政策時情地說道。
然而,近年來德國的經濟增長卻十分緩慢,很大一部分原因要歸結於製造業的萎縮與產品出口的疲軟。由此來看,在德國新任總統施泰因邁爾上臺之後,將會繼續貫徹默克爾的思想精神,加強中德雙方在汽車工業上的學習交流,或許大眾想要與華為展開的合作就是實現默克爾未竟事業的重要砝碼。
而當把視角切回到中國車企這邊,就會發現這是首次來自中國的企業在關鍵技術上佔領了絕對的制高點,並且同樣也是首次真正讓世界一流的車企甘願俯下身來向中國企業尋求合作的歷史性時刻。
遙想我國汽車工業發展之初,國有車企被迫需要以“市場換技術”的方式才能獲打破技術壟斷,而民資車企也動不動就花費數百億美元入股外國企業,這樣的例子大有人在。可實際上,截止目前為止,中國車企在傳統燃油車賽道仍在三大件上和外國車企有著難以逾越的技術鴻溝。
新能源汽車和智慧網聯汽車時代的到來,終於有機會讓中國的汽車工業和其他國家第一次站在了同一起跑線。
因此,對於“中國汽車工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句話,或許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解讀:其一是在產品層面,舊時代品牌積澱將一次性徹底推到重建;其二就是中外企業的角色互換,自華為與大眾坐上談判桌的那一刻就已經徹底改變。
龐大的企業看利益,偉大的企業拼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