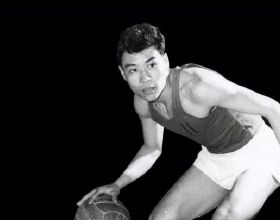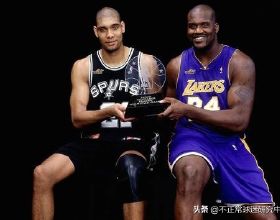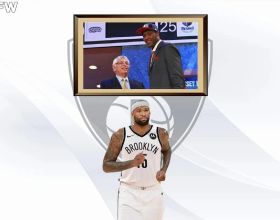似乎是很久之前就有人向我推薦李娟的書,但我一直未能拜讀。主要原因是當時還不太喜歡散文這種文學型別。
大部分散文是作者的一些感受,透過語言表達出來,為了描畫出場景或情感,免不了會堆砌辭藻,大段大段的排比句,即使名作家也不例外。讀書時遇到這種段落,我一般就瞄一眼,跳過去繼續如飢似渴地追情節了。
後來心靜了不少,也能沉下來讀讀散文了。跌宕起伏的情節看多了,也怪沒意思的,倒不如涓涓細流般的散文回味悠長。讀書口味的變化,或許也代表著進入新的人生階段了吧。
朋友推薦時我大概瞭解了一下,李娟的書寫的大都是發生在新疆的一些事。很慚愧一直搞不清新疆和西藏,對我來說,都是遙遠的邊疆,八百竿子也打不著。
能想到的對於那兒風土人情的印象,除了葡萄乾,就是路邊賣切糕的。我出生和工作的地方,都位於東部沿海,想來也產生不了什麼共鳴吧。
直到讀完將近一千頁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我意識到必須要讀讀短篇緩解一下,並且必須是輕鬆的、不費腦子的。於是去書城選了幾本,《冬牧場》就是其中之一。
作者在自序中說,“很多讀者說它是避暑神器,夏天讀最合適。”而我是在快過年的冬天裡讀的。雖是冬天,但因在深圳,夏天是那麼的酷熱和漫長,反而覺得是非常舒適的時節。
當我穿著一件T恤加薄外套,坐在桌前讀作者在去冬窩子前做的各項準備,最終確定了穿著的最終方案時,覺得莫不是誇張了些吧,怎麼要穿這麼多呢?
“下身從裡到外依次是:棉毛褲、保暖絨褲、駝毛棉褲、夾棉的不透氣的棉罩褲、羊毛皮褲。上身依次是:棉毛衣、薄毛衣、厚毛衣、棉坎肩、羽絨外套、羊皮大衣。再加上皮帽子、脖套、圍巾、口罩、手套。”
後來看到“溫度計的水銀柱都停在零下三十五度以下”,零下三十五度,是怎樣的概念呢?冰箱的冷凍室才零下十六度啊!
在冬牧場裡,唯一的水源是雪。有雪則有水,否則連飲用水都成問題。吃肉要冬宰,宰馬宰羊。城市裡的人,已經無法理解這種靠天生存的感覺了。無論春夏秋冬,開啟水龍頭就會有水,進到超市就會有米麵糧油、各類肉類蔬菜。
我們似乎忘了水來自江河湖泊,只知道是從自來水廠出來的;我們似乎忘了肉是從動物身上而來,只看到一塊塊整整齊齊地擺在冰櫃裡。天冷時躲進房間,開啟暖氣或空調。下雨時用機器烘乾衣服。天氣或許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但威脅不到生存了。
高寒天氣到來時,“最倒黴的怕是便秘的人吧……屁股會凍麻的……”,“晚飯時無論大家怎麼勸茶,我都打死不喝——怕起夜上廁所……”
我呆過的自然條件最艱難的地方,是出嫁之後每年要回的公婆家,那個位於大別山深處的小村落。公公婆婆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幾十年如一日地過著日子。
依然是用柴火做飯。廚房的灶臺上有一口大鐵鍋,用來炒菜煮米。圍繞著鍋的位置是大大小小几個鋁製的小鍋,裡面裝滿了水,做飯時燒柴火的熱量順便將小鍋裡的水加熱。離火最近的小鍋裡的水可以燒開,要倒進暖瓶作為飲用水。其他的水只是熱了,用來洗刷。
這些平時都夠用,可我們一大家子回去後,陡然多出了幾個人,但開水的量卻未能增加。在一次凍得瑟瑟發抖還沒熱水喝時,我用電熱壺燒了一壺,被公公發現,第二天電熱壺就消失不見了。
依然要去茅房。家裡雖已蓋了新房,但化糞池未修,新房裡的衛生間就是個擺設,大家都還保留著去茅房的習慣。而茅房,只是在豬圈裡挖了個供人排洩的坑,人的糞便順勢流下,和豬的混合在一起。
不知是不是水土不服,我一直拉稀。最怕的就是去上廁所,冷啊!凍得哆哆嗦嗦,後面還有豬的哼哼聲。緊張得連臭味都不在乎了。上完廁所,剛開始用盆子接自來水,兌點兒熱水洗手,後來熱水用完,只能強忍著涼用自來水。於是那個月例假時痛得死去活來。
忽然發現,作者平淡樸實的文字後面,蘊藏著巨大的勇氣和能量。我曾以為,這種文章沒什麼了不起,誰去經歷了都會寫出些東西來的。可,誰願意去經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