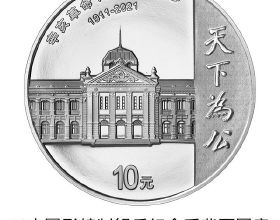這個事件揭示了年代測定的真相:“我們如何知道哪個標本是測年的優質標本呢?答案是,‘優質’標本會測出與進化論預設一致的年代。‘劣質’標本就是那些測出的年代與進化論不一致的標本——這是一個經典的迴圈論證。”
有一則頗流行的神話稱放射性元素測年法證實了地質年代表和人類進化論。這些測年法看似很高階,連很多基督徒都認同它們就是年老地球的證據。澄清這個錯覺的最佳辦法,就是考察一下東非KBS凝灰岩層和這裡出土的著名化石KNM-ER 1470。1
理查德·李基(Richard Leakey)是兩位著名古人類學家路易斯(Louis)和瑪利亞·李基(Mary Leakey)的兒子。他於1967年考察了肯亞北部的魯道夫湖(現在的圖爾卡納湖)的化石沉積層,並立即組織了一支遠征隊伍,尋找人科動物的化石。
在所有發現的化石中,最重要的要數KNM-ER 1470(顱骨1470)。這顆顱骨表面看上去很接近現代人的頭骨,但是理查德·李基最初推測它有290萬年的歷史。凱·比漢斯邁耶(Kay Behrensmeyer)是一位地質學家,早期曾與理查德·李基在東魯道夫一起工作。她在考察那片地區的地質結構時,發現了一層由火山灰構成的地層或稱凝灰岩,後來被命名為凱·比漢斯邁耶場(即KBS凝灰岩)。如果這層KBS凝灰岩是位於其它地方,就不會引起人們關注。但在東魯道夫這個地方則意義非常。第一,一般情況下,放射性測定法不能用於人的化石和文物(工具),但是可以用於KBS凝灰岩,因為它含有鉀-40,而鉀-40會衰變為氬-40。第二,有些出土的石制工具與KBS凝灰岩相關聯。人們假定,利用凝灰岩則可估測石器的年代。第三,在KBS凝灰岩以上的和以下的地層都出土了數百件智人和南猿的化石。因此,這層凝灰岩的年齡就成了在它之上的化石的最大年齡和在它之下的化石的最小年齡。第一次對KBS凝灰岩進行放射性元素定年是在1969年,遠遠早於發現顱骨1470的時間。理查德·李基將岩石標本提供給鉀-氬測年法的權威人士F.J.菲奇(F.J. Fitch,倫敦大學伯克貝克學院)和J.A.米勒(J.A. Miller,劍橋大學)。菲奇和米勒第一次測得的結果是2.12到2.30億年,符合進化論的要求。然而關於這一結果,他們表示:“這些結果清楚地表明,這裡有外在因素造成的氬元素年齡差異….”。2他們怎麼知道存在差異?這是根據伴隨著岩層出土的化石得出的結論。雖然我們一再被告知,測年法能夠獨立地證明進化年代,但是事實上,與地層相關聯的化石已經決定了估算出來的“可接受的”年齡。根據他們的進化觀點,出土於KBS凝灰岩層之下的南猿和其他哺乳動物化石足以決定這岩石層應該有200到500萬年的歷史。所測得的2.12到2.3億年的結論實在是謬以千里。如果沒有與地層相關聯的化石,根據這一測年法得出的結論是對是錯,相信進化論的地質學家將無從知曉。在沒有化石作為參考的其它情況下,相信進化論的地質學家就會把根據放射性測年法估算的年齡當作正確的答案。菲奇和米勒要了新的標本,於是他們根據這些浮石團和長石晶體得出新的結論:KBS凝灰岩有261萬年的歷史。3李基於KBS凝灰岩之下的岩層中發現了顱骨,而KBS凝灰岩的測定年齡為261萬年,顱骨下面的岩層的年齡被定為318萬年,因而顱骨的年齡被估算為290萬年。1972年,在顱骨1470被公開之前,維森特·馬格里歐(Vincent Maglio,普林斯頓大學)在《自然》期刊上發表了魯道夫湖泊東邊埋有人科動物的沉積岩的年代表,其中包括KBS凝灰岩。4 該年代表的根據是兩種豬和一種象的演化譜系。馬格里歐的年代表和菲奇-米勒的測定結果一致,並被認為是證實了他們測得的年代。1974年,《自然》雜誌釋出了這片地區的第三份年表,這次的根據是古磁場。5 270萬年到300萬年的結論似乎已經成為了聯合其它定年法的‘軸心’。6到1974年末,人們使用了四種不同的測年法,對KBS凝灰岩做了五次年代測定。據說不同測年法得出了互不衝突的結果,這似乎是地質學家夢寐以求的。然而,在臺面以下, 這個被確定為290萬年的頭骨1470讓進化論界難以接受。按照人類進化理論來看,一個與現代人如此如此相似的顱骨不可能那麼古老。可是理查德·李基卻一直堅持他最初測出的年代。如果顱骨1470真有290萬年,那麼他就發現了人屬中最為古老的成員,否則他的發現就沒有多大意義!因此,他拒絕降低這顆顱骨的年齡。與此同時,另外一份由G.H.柯提思(G.H. Curtis)和他的同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完成的研究則稱凝灰岩有兩個獨立的部分。其中一個年齡是160萬年,而顱骨1470出土的另一個部分,年齡是182萬年,兩個年齡都比之前五次研究釋出的年齡要低。以上引用的所有文章都稱,要獲得沒有受到干擾、風化或是再生巖的岩石標本或晶體標本,困難重重。問題是,我們如何知道哪個標本是測年的優質標本呢?答案是,‘優質’標本會測出與進化論預設一致的年代。‘劣質’標本就是那些測出的年代與進化論不一致的標本——這是一個經典的迴圈論證。1980年的三月20日,又有兩份發表於《自然》中的測年法研究對之前的研究成果提出批判,並稱KBS凝灰岩的年齡是187到189萬年。1981年末,伊恩·麥克德哥(Ian McDougall)發表了一份關於KBS凝灰岩的研究,稱凝灰岩的年齡是188萬年。而那時,KBS凝灰岩測年結果的爭論已經持續了10年,最後,大家一致同意一個距我們更近的日期。
豬的力量
雖然看上去KBS凝灰岩的爭論是在1980-1981年間被不同測年法測得的結果平息的,但事實上,這個爭議是在1975年被豬平息的。唐納德·約翰森(Donald Johanson)回憶了1975年參加倫敦人類學和地質學主教會議的經過。當時巴茲爾·庫克(Basil Cooke,哈利法克斯戴爾豪斯大學)發表了一份重要研究報告。他的研究是針對南衣索比亞,包括哈達爾地區(衣索比亞)和奧杜威峽谷(坦尚尼亞)地區的豬基因序列。據庫克的研究,以前對圖爾卡納湖(即從前的魯道夫湖)的定年比實際年齡高出了80萬年。這是他從圖爾卡納的豬得知的。關於會議進行的情況,約翰森寫道:‘除了圖爾卡納湖團隊[理查德李基和他的研究夥伴],所有人都同意KBS凝灰岩以及頭骨1470的年齡需要更正。’7整個事件驚人的部分在於,古人類學家拒絕了他們一般認同的客觀、科學資料。幾份研究都具備內部一致性,五種不同定年法測得的結果非常接近。但是唯一的問題就在於,這些年代無法與豬和人的進化理論相融。豬的進化貌似簡明地了結了東非KBS凝灰岩測年問題,但是證據卻無法令人心悅誠服。在庫克提出的豬種系發展史中(非洲灌叢野豬、巨林豬、疣豬等),他將豬分成了三個分類學上的“群”。其中兩個種群起源於“假想的豬類祖先”。組成這個三個群的20個品種的譜系相互平行,中間僅用虛線連線,表示任何兩個物種之間的血緣關係尚沒有得到證實。這張圖也完全可以由創造論者繪製出來。很多豬化石證據都是牙齒。有幾個種類是基於非常薄弱的證據上(“不完全知道”、“罕見”、“稀少”等),各種關聯大都是出於猜測。1980-1981年出版的關於KBS凝灰岩年齡的研究論文中有太多對早期研究的批判,以至於他們不得不質疑自己使用的測年方法的客觀性和有效性。
放射性測定法的神話
從上文所述的經過中可以突出地看到放射性測年法有兩個嚴重的問題。首先,對KBS凝灰岩進行年代測定的歷史說明,無論科學家如何嚴謹地選擇岩石標本和進行實驗操作,只要他得出的結論不是“正確的年代”,都會被指控為用了受干擾(受汙染)的標本和有誤的方法,而這些指控卻不需要證據來證實。文獻顯示,即便放射性元素測年法的理論成立(其實不然),要在實際操作中找到純淨的、未受汙染的岩石標本,也需要人類所不具備的無所不知的能力才能實現。放射性元素測年法是一個自欺欺人和迴圈論證的經典例子。這是進化論的又一個迷思。
第二,一般情況下,都是先發現化石,接下來人們對化石出土的岩層進行測定。在這種情況下,古人類學家在某些程度上就可以對結果有一些控制。他可以拒絕不符合化石進化的年代。他甚至都不需要發表那些“異常錯誤”年代。這麼做的結果,就是繪製一副看上去非常符合人類進化論的人類化石記錄圖景,實際上卻在誤導人們。
如果顱骨1470沒有被發現,KBS凝灰岩就很可能被定為261萬年。科學家就會告訴我們,因為放射性測定法的準確性,又因為有幾種獨立的測年法的控制,這個結果是一個“保險的年代”。這顆與現代人十分接近的顱骨1470是一個非常驚人的發現,而它剛好處於KBS凝灰岩下方,從而促成了長達十年的爭論。
在這樁長達十年的關於一個至關重要的人類化石的年代之爭中,最後還是豬勝出了。豬打敗了大象,打敗了鉀-氬測年法,打敗了氬40/氬39測年法,打敗了裂變徑跡測年法,打敗了古磁場。豬大獲全勝。但是,實際上,獲勝的並不是豬,而是進化論。在測年的遊戲中,進化論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參考文獻和註釋
- KNM-ER 1470:KNM代表肯亞國家博物館9(Kenya National Museums),這是它珍藏的地方;ER代表東魯道夫(EastRudolf),這是它出土的地方;1470是博物館收藏號)。
- F.J. Fitch and J.A. Miller, ‘RadioisotopicAge Determinations of Lake Rudolf Artifact Site’, Nature 226, April 18, 1970,p. 226.
- 同上, p. 228.
- Vincent J. Maglio, ‘Vertebrate Faunas andChronology of Hominid-bearing Sediments East of Lake Rudolf, Kenya’, Nature239, October 13, 1972, pp. 379–85.
- A. Brock and G. Isaac, ‘Paleomagnetic stratigraphyand chronology of hominid-bearing sediments east of Lake Rudolf, Kenya’, Nature247, February 8, 1974, pp. 344–8.
- 同上, p. 347.
- Donald C. Johanson and Maitland A. Edey, Lucy:The Beginnings of Humankind,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1981, p. 240.Bracketed material added for clarity.
經許可轉自國際創造事工Creation.com,歡迎轉發,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