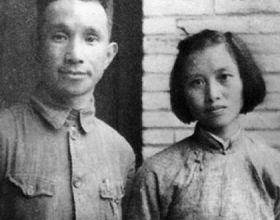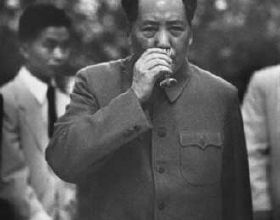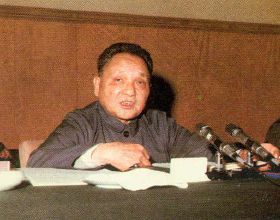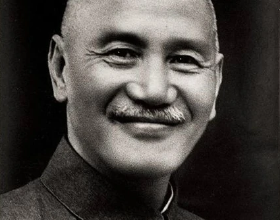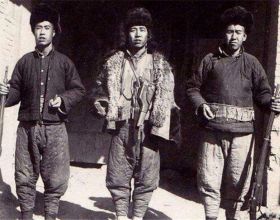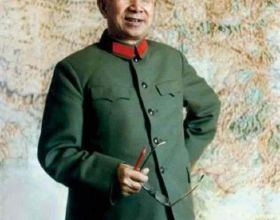1870-1871年的普法戰爭堪稱“火與馬的時代”末日篇章,雖然它在德、法、英、俄都得到了相當的重視,但關於它的靠譜中文材料同樣稀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2020年出版過美國學者瓦夫羅(Wawro)的《普法戰爭》,可以說是開了一個好頭,不過,就軍事分析層面而言,中文裡最好的材料大概還得算是陸軍大學教官多馬舍夫斯基出版於1944年的遺著《普法戰史》。
正如其姓氏所示,多馬舍夫斯基來自俄羅斯帝國西部沃倫地區(今烏克蘭沃倫)的俄化波蘭貴族家庭,全名為弗拉季斯拉夫·利奧波多維奇·多馬舍夫斯基(Владислав ЛеопольдовичТомашевский),姓氏的波蘭文寫法則是托馬謝夫斯基(Tomaszewski)。
多馬舍夫斯基生於1882年,接受過完整的軍事教育,先後畢業於波爾塔瓦軍校(1899年)、康斯坦丁炮兵學校(1902年)和尼古拉耶夫軍事學院(1914年),參加過日俄戰爭、一戰和國內戰爭,以白衛軍少將身份戰敗後流亡中國,曾和布林林(Петр Гаврилович Бурлин)一同就任張作霖高參,對奉軍炮兵建設有所貢獻。東北易幟後,多馬舍夫斯基與布林林輾轉進入陸軍大學任教,得到歷屆學員的高度評價,抗戰期間病逝於重慶。[1]
[1] 關於多馬舍夫斯基(托馬舍夫斯基)、布林林(布林霖)等白俄教官的生平,除了陸大相關學員回憶外,還可參見斯米爾諾夫的論文《俄國流亡軍人在中國(1920-1940年代末)》(Русская военн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в Китае (1920 – конец 1940-х гг.))。
多馬舍夫斯基在陸大教授戰史、動員等科目,也積極向學員傳授當時各國最新軍事學術進展,曾用俄文撰寫普法戰史講義,並由吳保泰譯成中文供教學使用,去世後講義整理出版為《普法戰史》一書。
筆者特此整理錄入《普法戰史》中分析1870年8月18日聖普里瓦(書中作聖卜利瓦)會戰部分,以饗讀者,書中特有用詞除軍和軍團外均不做更改,僅在首次出現時給出對應的現代說法。
八月十六日,溫維裡(Vionville,今譯維永維爾)發生激戰。德方第三軍(*)司令為阻止敵人之退卻,於晨八時決行攻擊。傍晚,戰鬥終止,雙方各以為獲得戰術上之勝利,然戰略上之勝利,當然屬於德方。無論如何,德軍已進據法軍退赴凡爾登之路線,是已完成應完成之任務矣。
(*)吳保泰等譯者依然沿用日系習慣,文中軍團實為現代軍語中的軍(Corps d'Armée),軍反而是集團軍(Armée),亦即軍是軍團的上級單位,鑑於容易造成誤解,相關內容均直接修改。
雙方軍隊之特點,此役中重複表現者,與前數役中吾人所見者如出一轍,此雙方交戰國軍制之直接後果也。
至於法軍總指揮巴善(Bazaine,今譯巴贊)之行徑,則在當時已極離奇。巴氏迄不能為堅定之決心,突圍赴凡爾登乎?抑退歸麥次(Metz,今譯梅斯)乎?於此極端相反之決策,竟依違兩可,不能自決就其種種行動觀察,至八月十六日,巴善心中已決定困守麥次。適法皇拿破崙於十六日晨離開麥次,巴氏更成為全體總指揮。
精神喪失,百事皆休。果法軍統帥之心事已為困守麥次,則十七日十八日繼為之戰鬥,實無謂之“屠殺”,直無異自殲其精銳之士卒耳。
十六日夜間,法方軍隊已完成繼續作戰之準備,靜待後命,或作戰,或續退凡爾登。乃所奉命令為變更配置,右翼後撤。於是法軍所佔陣地,以麥次為後方,前方則轉向本國。變更配置時,秩序大亂,但德軍因十六日之戰與前數日之行軍,疲乏萬分,未加擾害。
十八日戰鬥前,巴善所據陣地,相當堅固。
德方第一軍團、第二軍團於麥次以南渡摩塞爾(Moselle,今譯摩澤爾)河後,採北向陣地,與法軍陣地成直角,德軍司令部對法軍狀況殊欠明瞭,遽擬對法人進擊,包圍其北邊之右翼。斯時德軍應為之機動極繁難,一面應遂行攻擊,一面須移轉陣地。
種種錯誤,使德軍司令部誤認法軍陣地展延僅五公里,止於孟清仰格蘭(Montigny-la-Grange,今譯蒙蒂尼拉格朗熱或蒙蒂尼農莊)。故其戰鬥計劃,系以第一軍團攻擊法軍正面,第二軍團攻其右翼。因諜報之誤,第二軍團所臨陣地,竟非法軍右翼,而系其正面。德方第九軍行抵維爾聶維裡(Vernéville,今譯韋爾內維爾),力攻孟清仰格蘭之法軍,是時軍團司令因急於進攻,未俟鄰軍近衛軍開到,即行開火。正午時分,第九軍各炮兵連開始射擊,至是始知德軍竟未能包圍法軍而自陷於北來法軍包圍之中,猛烈炮火,直向德軍側翼與後方轟擊,使第九軍炮兵陷於極艱難之境地,一部分炮兵被迫停止射擊,一部分為法軍奪去。於是第九軍岌岌可危,軍團司令官因第九軍長之請,立派預備隊之近衛軍第三旅前往增援,另一方面,近衛軍正在迤北之聖卜利瓦(St. Privat)方面作殊死戰,其力量因此減弱。生力軍近衛旅馳到第九軍陣地後,實行衝鋒,事前則無炮兵之準備,衝鋒旋遭擊退,損失極巨,其狙擊營官長全部傷亡。其後第九軍方面戰況漸弛緩,入夜以後,始知法人已退往麥次,蓋聖卜利瓦經近衛軍與第十二軍(薩克森軍)之合攻,已被德人佔領矣。
第九軍過急於開火,致蒙不利。不自行偵察敵人側翼先在何處,誤依軍司令部不正確之情報妄定方位,故其所施攻擊雖極猛勇,但毫無目標。近衛旅之衝鋒亦然。倘敵人態度積極,則德方必輕輕斷送其炮兵,而全軍亦發生極端嚴重之恐慌矣。德方第一軍團方面之戰事,戰術上亦屬不利。該處德軍亦未行搜尋,即由騎兵進擊,失利後造成全軍大混亂。
近衛軍奉令協助第九軍,攻擊其迤北之敵,向樂庫耳(Roncourt,今譯龍庫爾),聖卜利瓦前進。第十二軍(薩克森軍)應在近衛軍以北進攻,俾迂迴法軍之右翼。第二線,近衛軍以後,為第十軍,作支援之用。
普方近衛軍進攻聖卜利瓦,在戰史上極具興趣。普方第一近衛師奉派開赴聖馬麗阿申(Sainte-Marie-aux-Chênes,今譯聖瑪麗-歐謝訥)村進擊該村之法軍陣地,旋與薩克森軍協力將法人由該村擊出,即隱匿該村休息達一小時半之久。斯時,其右方(自聖馬麗阿申至喀崩維裡(Habonville,今譯阿邦維爾))之近衛軍之各炮兵連業已展開,而薩克森第十二軍之炮兵則展開於聖馬麗阿申之西北。
法方為喀拉畢(Canrobert,今譯康羅貝爾)統率之第六軍,據聖卜利瓦村。該村居高臨下,在當時之軍事意義,乃一陣地之“鑰”。聖卜利瓦共駐法軍步兵十四營。
下午五許,聖卜利瓦以北法軍炮兵,因受德方炮火壓迫,發炮漸稀,而步兵頗有逐漸放棄其最前線之戰壕者,是種情況使德近衛軍司令疑為法軍已開始退卻,而擔任包圍之薩克森軍或將捷足先登,則佔領聖卜利瓦之榮譽將不為近衛軍所有,而近衛軍之體面何存,故近衛軍司令立下令自正面攻擊敵人、第一師由公路之北前進,第二師由公路之南前進。
第一師師長帕別(Pape,今譯帕佩)是日晨曾與第三軍司令相晤,後者曾於十六日與法人激戰,因告前者曰:“吾人估計法人沙司普(Chassepot,今譯沙瑟波、夏斯波)之火力嫌低。進攻時,切不可一仍練兵時所習之戰術,應多采運動戰,雖地上極小之掩蔽物體,亦應儘量利用……法人對其側翼威脅之感覺,甚為靈敏。”然普魯士近衛軍傳統觀念與此忠告適相扞格,故第一師師長終不能採納。
下午五時四十五分,近衛軍第一旅由聖馬麗阿申移動,繞村南前進。前進時,各團列為預備縱隊,其先遣散兵共僅四排。前進之初,距敵共僅一千五百米,各團已在敵步兵火勢力下,透過該村後,距敵約一千米遠近,隊形開始旋迴,俾進據公路北之攻擊地帶,公路兩側原有深溝,又滿植樹木,透過時,敵步兵火力大肆威力,已極困難,兩翼各連復遵照操典賓士前進,德國近衛軍操練時前進方式即系如此。此在平時固為拿手好戲,然於戰場演出,其結果自不堪問,結果隊形大亂,四散奔竄,指揮失效。一部趨聖卜利瓦,一部奔樂庫耳,各自為政。迨近衛軍近至距敵五百米遠近之時(德之長針槍至是始有效用),各團所剩人數,皆僅三分之一,其餘非死即傷。第一旅後之近衛軍第三團所受損失亦相等。
近衛軍近至距敵二百步遠近,即不能再進。
失利之教訓,立使近衛軍指揮部變更方法,迨第四團前進時,已知盡力利用可資隱蔽之地形。軍區司令暨師長等均改持慎重態度,令部下存網前進,不必匆忙,炮兵先任破壞工作,以為步兵衝鋒之準備,前此近衛軍懼薩克森軍先完成迂迴,而進佔聖卜利瓦,現竟向薩克森軍求援,遣一軍官馳往,告以協攻路線。前此近衛軍司令拒絕其後方第十軍炮兵之援助,現亦派人向之求救。晚八時開始總攻擊。攻擊之經過,甚無秩序,一部分自相擾害,一部分竟向己方射擊,但入晚後終將聖卜利瓦佔領。迄次日晨,秩序仍未恢復,斷續槍聲,時有所聞,然事實上此種總攻,已屬多事,蓋法方守聖卜利瓦之軍司令喀拉畢已下令撤退麥次矣。撤退原因並不在近衛軍之進攻,而在薩克森軍之迂迴。進據聖卜利瓦時所遇者,僅法軍之後衛而已。
總計德方近衛軍第一師損失官長一百五十人,兵卒三千七百一十七人,此在當時,實為極巨數額。此項損失毫無益處,徒表示德人於此役中輕視步槍火力與防禦戰之優點耳。
吾人於此可知軍事上保守主義勢力如此偉大。保守主義原自有其健全之基礎,故吾人所見信奉保守主義者多為優良英勇之軍隊,軍事上施行某種不經見之事物,以代替舊有著名之物,每不免冒若干危險。所可慮者。健全之保守主義,事實上每易流於“守舊”,而阻礙進化,制動器對於列車或汽車之效用,固無人敢予否認,然即以制動器為機械之基礎,則殊為大錯,軍事亦然……
上述聖卜利瓦一役,苟就其外表言,近衛軍固已達到目的,然實際上非近衛軍決定戰鬥之命運,而系薩克森軍迂迴運動之力。近衛軍激戰無功之原因,即在近衛軍輕視膛線步槍之火力。膛線步槍使防禦方面獲得絕大優勢,足使步兵單獨之攻擊為不可能,必得炮兵之準備支援隨伴而後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