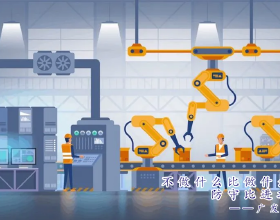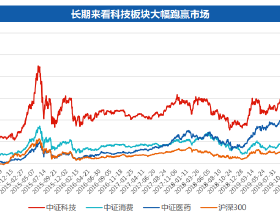有人說:“一個人,一輩子,一定要去一次西藏。”,還有人說:“人一生要去兩次西藏,第一次是自己去,第二次是帶著自己心愛的人去…...”
那到底西藏有什麼神秘的呢?景色就是比其他地方好麼?天,就是清澈湛藍麼?空氣,就比其他地方新鮮嗎?
答案,都是。
在這裡,可以穿越時空的牽絆,在這裡,可以洗滌心靈與靈魂。這裡是離太陽最近的地方,是伸手彷彿可以觸及星星的天堂。
是不是沒去過的人都心生嚮往,去過的人則念念不忘?
今天,本文的主人公來給你講述他的第一次西藏之旅,一次刻骨銘心的生死經歷。
講述人:曉光 60歲
2006年7月底的一天,✘✘旅行社的總經理鄭邕(化名)給我打來電話說,他將於8月初去考察剛剛開通的青藏鐵路,問我是否有時間與他同行。
對於年逾不惑的我來說,那片雪域高原,以她的神秘和安詳,累積著我從少年到壯年20多年的幻想與渴望;而今,我終於有機會去領略她的美麗,自然我不會拒絕在如此美好的季節裡的一個如此美好的建議。
我沒料到,從那時起的一系列變化和差池,最終鑄造出一個個錯誤,使得我的青藏之行代價高昂,愈顯悲壯。
計劃變更
8月1日,鄭邕打電話告訴我,旅行計劃已經全部確定,時間不變,但行程有些調整,按原計劃倒著走。
原來他擬定的是一條青藏高原的黃金旅遊線路:我們在成都會合後,飛西寧呆一天,然後由青藏鐵路進入高原,在拉薩住三晚後飛回成都。這樣的線路設計,可以在2200米海拔的西寧呆一天以適應高原氣候,然後逐步爬升在進藏,沿途領略魅力無邊的高原景色。對初次進藏的人來說,這樣的線路最容易避免高原反應,而且一旦出現高原反應也容易輕鬆離開。
誰都知道這是一條黃金旅遊線路。正因如此,在這進藏的黃金季節裡,又恰逢青藏鐵路剛剛開通,身為全國百強旅行社總經理的鄭邕一時半會也無法弄到西寧至拉薩的火車票。情急之下,他決定:倒著走。
我相信,如果不是計劃的變更,不會有以後的故事。
兆頭不好
8月2日晚,我如約啟程,坐晚班飛機赴成都與鄭邕會合。依我的經驗,晚班飛機晚點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9時10分的航班沒到9時就叫登機了。9時10分,機身動了動,似乎就要起飛,但很快就沒了動靜。過了一會兒,乘務員通報,因桂林機場下雨,飛機延時起飛。
飛機飛了一整天,因種種原因晚上不能正點到港,造成航班延誤,我不難理解。可這回怪了,飛機上了,安全帶繫了,飛機不飛了,我心裡隱隱有點怪怪的感覺。
正想著,鄭邕來電話了:司機已經去機場接你了,你那兒下雨飛機晚點,你別急,你不到司機不敢走的。我心中淡淡一笑:訊息挺靈、口氣挺大。百強社老總嘛,這話他不說,誰說?
當時我並不知道,就在等我而無聊的這段時間裡,鄭邕和一幫正在歌廳裡玩的朋友因我的晚到而安排了“下一個節目”,而這個安排則成了整個故事的導火索。
老夫輕狂
晚點近一個小時後,午夜12時我走出了成都雙流國際機場,司機把我帶去一個露天夜市與鄭邕會合。
這是一群剛過而立之年也的確事業略有成就的年輕人,春風得意,恣意豪放。反正沒有女士在場,而且喝酒又是男人的事業,五、六個大男人接二連三地脫光了膀子,我也不知廉恥地露出了一身的贅肉。
夜越來越深,我愜意地享受著大夥兒左一聲“大哥”、右一聲“老兄”的招呼,一杯接一杯地灌著啤酒,志得意滿地接受著一眾小兄弟的敬意,在眾星捧月的氣氛中,儘管夜風越來越涼,可我飄飄然的心卻是越來越熱。
凌晨5時,我和鄭邕搖搖晃晃地回到酒店。7時,我們又急急忙忙起床,趕早班飛機飛向雪域高原。
川人說,感冒不上山。但是,事後我敢確信,在那個晚上,我為自己的輕狂付出了代價:著涼了ー一但我當時卻渾然不知。
姿意高原
帶著一顆“定時炸彈”的我,一點都不知道感冒與高原結合的危險。
一下飛機,拉薩天藍雲淡、異域風情便深深陶醉了我。親人和朋友打電話來,我十分愉快地告訴他們:“感覺好極了,景色美極了!”妻問我:“天很低嗎?”我說:“那邊山頭有一朵雲,我爬上去就可以摘下來。”說實話,我並不僅僅是為了讓關心我的人放心,當時我的的確確就這感覺。
因為布達拉宮限制參觀人數,當我們好不容易從旁門左道搞到門票時,已經到了進宮時間,而一旦超過20分鐘,門票就會失效。因此,我們是一路小跑著進入布達拉宮的。一進去,感覺一身都是汗水,溼透了,於是找一塊蔭涼的地方歇一歇,高原的雪風(拉薩四周都是雪山,風是涼的)一吹,涼嗖嗖的,舒服極了。於是,我如法炮製,一會熱一會涼地登上了海拔3700多米的布達拉宮,陶醉於她的金碧輝煌。當時我不知道,那一陣陣的涼爽,便是高原對我的一次次溫柔懲罰。
第二天去那木錯,一下車就被絕世美景深深震懾:頭頂藍天嬌豔嫵媚,遠方雪峰素雅聖潔,眼前湖泊銀浪似海。我想快一點親近這份美麗,於是順著面前的一個高約1米的緩坡,一溜煙衝了下去。這僅僅是海拔4700多米高原上的一個小小的衝動,但胸悶氣喘的感覺迅速象山一樣壓了過來。從此,這種感覺一直或輕或重,始終陪伴著我的整個高原旅程。
從納木錯回到賓館,連鄭邕都已疲憊不堪。我們誰都沒胃口吃東西,一致同意睡覺。晚9點多,鄭邕餓了,叫出去吃飯。對著滿桌子的美食佳餚,他盡情享用,我卻索然無味。
我深深體會了高原的神秘與安詳。她笑容可掬地看著你在她的懷抱中縱情山水,恣意妄為。每一個到過青藏高原的人都知道:你想跑、你想跳、你想飛!但你如果真跑了、跳了、飛了,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一一高原就是這麼奇怪,她鼓勵你思想,卻約束你行動。
一錯再錯
6日晚上,是我們在拉薩的最後一個晚上,厭食、乏力等症狀已非常明顯,但我還以為是旅途太勞累了,以為睡一覺就會好了,於是早早就躺下了。
凌晨兩點,我怎麼也睡不著了,偶爾還有喘不過氣的感覺。我們住的拉薩飯店是四星級酒店,床頭就有氧氣裝置,我卻一次次地制止了自己使用它的慾望,因為我擔心一旦用上它,就再也離不開它。我在問自己:是否該去醫院一趟?最後我自己作出了一個決定:早上去乘坐火車時買點阿莫西林就行了,我這麼棒的身體,沒什麼大事。
凌晨5點,我們起床收拾行裝,慢吞吞地在酒店吃了早餐,7點半走出酒店,離青藏列車發車還有半小時,按計劃我還可以順道買點藥,鄭邕說,火車站離布達拉宮不遠,坐計程車10分鐘就可以到了。
但計程車司機把我們嚇了一跳。他告訴我們,火車站距離拉薩有20多公里,現在時間已經很緊張了。我哪敢再說買藥,鑽進車裡便叫司機快快趕往車站。一路過去我才知道:拉薩火車站距離布達拉宮的確不遠,但中間隔著拉薩河,要從遠方的大橋繞道過去。
一路催促司機“快開快開”,到了車站後趕緊拎上大包小包,既不像跑又不像走地衝進了車站。好不容易氣喘吁吁地到了站臺口,一看乘務員已經在東張西望地準備關車門了,我只好垂死掙扎著撲向自己的車廂一一我相信,這一番折騰,即便是在平原我也好幾年沒有領教過了。
停車搶救
列車剛開,乘務員就送來了氧氣吸管,進藏列車都有氧氣裝置。我拿來插上,好玩似地吸了一會,就拔了下來,我心心念念著沿途下車看風景呢,可不想依賴這玩意。
下午2時50分,車到那曲,海拔4500米,鄭邕說一聲“下去看看”就離開了車廂。我不甘示弱,跟隨其後也走出了車廂。但是,我在這個高原車站的行走距離不會比初登月球的宇航員更多,我甚至還沒能看清楚這個高原車站的景緻,山一樣的壓抑感就將我逼回了車廂。
我再也支援不住了。於是,我告訴乘務員我需要醫生。
不一會兒,兩位中年女醫生拎著急救箱來到了我身邊。她倆迅速進行檢查,讓我吸上她們帶來的純氧,一臉嚴峻地告訴我懷疑是肺水腫,並很快就給我掛上了點滴藥水。又過了一會,年輕的列車長也來了,醫生對他說,必須立即將我送下火車迅速搶救。從他們談話中我瞭解到,再過20分鐘將經過沱沱河站,那裡有個高原急救站,火車正常行駛並不停靠,再往後必須到400多公里外的格爾木才有醫院了。很快,運轉車長也來了,他們一大波人全忙翻了:運轉車長在跟鐵路局聯絡,醫生在找鄭邕談話,列車長在填寫各種表格,護士在不停地給我量體溫測血壓,好幾名乘務員則默默地站在走道上面色嚴峻地望著我。
很快,有結果了:列車幾分鐘後將臨時停靠沱沱河車站,鄭邕在簽字摁手印,幾名乘務員則忙著幫助收拾行李。我還保持著幾分冷靜,問醫生:“有救護車到站臺上來嗎?”她說有。我又問:“真有必要下車搶救?”她說絕對有必要。我想,投資800個億的青藏鐵路應該有個裝備挺好的高原急救站,下車可能會更安全一些,於是我就接受了他們的安排。
事後我才知道,醫生很嚴肅地告訴鄭邕,基本上可以肯定我患上了高原肺水腫,並出現了腦水腫先兆,如果出現腦水腫,幾分鐘就會威脅生命,即使搶救過來,也別想再當記者了一一因為腦子會壞。
車停了,我拔掉氧氣走出車廂,驚訝地發現停在站臺上的不是救護車,而是一輛皮卡車。列車上的醫生沒有下車,司機是一名穿鐵路制服的人,他將我扶上了汽車。我問他:“急救站在哪裡?”他說:“不遠,前面大概3公里。”
我發誓:在我生命的未來日子裡,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這十分鐘!
這是怎樣的一幅情景:在巍峨崑崙山海拔4500米的三江源,我這個生命垂危的肺水腫病人,在毫無醫療保護的情況下,乘著一輛皮卡車駛向幾公里外的高原急救站,頭疼欲裂,呼吸越來越短促,那是我生命的諾亞方舟嗎?
千里“空降”
唐古拉山鎮角落一個普通的小院落,一排極普通的平房,我怎麼也想像不到那便是青藏線上的生命守護神一一沱沱河急救站。我更想像不到的是,它的急救室不是在入口處,而是在一條長長的過道的幾乎盡頭,而且醫生還一臉茫然地看著我到來。
如此地缺乏專業素養,我的心冷慘了。我想,多年來,雪域高原讓我魂牽夢繞,這回我可能真要魂系高原了。
很快,年輕醫生(後來我知道他姓包,工作剛4年)憑他嫻熟冷靜的專業操作,讓我漸漸地平靜了下來。在他給我注射的時候,我甚至有閒心誇獎他護士的工作也做得不錯。他瞪了我一眼,不無抱怨地說:“我們這裡醫生、護士的工作從來都是一個人做!”
4500米的海拔,如此簡陋的醫療條件,這裡絕非久留之地!幾個小時以後,我的病情趨於穩定,在我的一再堅持下,急救站和它所屬的海西州第二醫院同意了用救護車將我送到山下的格爾木,那裡的海拔只有2700米,雖然這意味著我們將驅車400多公里,並翻越海拔4800米的崑崙山埡口。
我知道這段旅途充滿風險,我親自簽了字。我沒有仔細看那份檔案中寫了些什麼,只是記得有兩個字:猝死!親愛的讀者,千萬別以為接下來的旅程如何驚心動魄、蕩氣迥腸,實際上那更象一次極其普通的輕鬆愉快的高原汽車旅行。
我們離開急救站時已近晚上10時,鄭邕坐在副駕駛位上,我和小包醫生在車廂。車開動不久,我叫小包遞一罐“紅牛”飲料給我,讓他自己也喝一罐;又過了一會,我拿出香菸讓他吸,他有些猶豫,我告訴他“沒關係,我已經沒事了。”也許是因為我將生命託付給他的那份坦然,也許是我在言談舉止間滲透出了從容,小包說,“你是我救治的病人中心理最穩定的一個。”逐漸我取得了他的信任。他給我講他的愛情故事:大學熱戀的女友去年結婚了,新郎不是他......
鄭邕久不久回過頭來關切地看一看我這邊的情況,見我精神挺好,這小子心裡開始活泛了起來。他跟司機說著話,不時驚叫兩聲。我知道,這傢伙不是看到了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就是野駱駝什麼的,弄得我心裡癢癢的。更過份的是,他還敢置我的生命安危於不顧,兩次叫司機停車片刻,他自己或者豪情萬丈地在崑崙山埡口領略高原風光,或者獨自心安理得地去欣賞“崑崙神泉”。我咬牙切齒地想,俺這回是動不了身了,下回俺來崑崙山一定得叫這小子買單。
我還給他們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鄭邕對司機說:“累了吧?如果我會開手動檔車,我就可以替你開一會了。”我接上話說:“我開得了,我來吧!”他們誰都不理我。
就這樣,我們星夜賓士6小時,行程近千里,“空降”2000米。8日凌晨,我住進了海西州第二醫院(原鐵路醫院),我基本脫險了。
其實,在那段浪漫的旅程中,我一直都清醒地知道:如果那輛半新半舊的救護車隨便壞個什麼零件,我壞的可就不是一兩個“零件”了。
勝利“逃亡”
天一亮,醫院的王院長就趕來看我。我很誠懇地對他說,我個人並不想追究醫院什麼責任,但是,在沒有救護車的情況下,讓我在沱沱河下車,在如此嚴苛的環境中有十分鐘時間失去任何醫療保護,是非常危險的措施。作為一名記者,我希望醫院能汲取教訓,千萬不要讓另一個生命遭遇同樣的危險。王院長也很誠懇地表示要總結經驗教訓。
醫生們要求我再住院治療兩天,我則堅持當天離院返家。見我去意已定,醫生們嘴上沒有答應,但還是默默地在用藥和備藥上作了一些準備,我看眼裡,心裡十分感動。
下午4時許,我辦了個自行離開醫院的手續,登上了格爾木開往西寧的火車。鄭邕幫我準備了3個大大的氧氣袋,堆滿了我的臥鋪鋪位。他還直嚷嚷:“買10個就好了”。因為這一路火車要走15個小時,海拔大多是3000至4000米,對於我這個尚處危險中的人來說,心裡可真沒什麼底。
那個晚上鄭邕可不輕鬆。因為我不能排除睡著了就不再醒來的可能,因此他一夜都坐在車窗邊眼睜睜地看著我,直到將近凌晨5時,火車開始下山,他才到自己的鋪位躺下。早上7點,列車到達了海拔2200米的青海省會城市西寧,車都停穩了,車上人群喧譁,鄭邕仍在呼呼大睡。我不得已將他搖醒,他一激凌彈坐起來,愣愣地望著我,那呆呆傻傻的模樣讓我煞是感動。
9日上午10時,我們從西寧飛往海拔500米的成都,徹底脫離了高原險境;當晚,我即飛回了桂林。
在成都分手時,鄭邕哭了。我們之間聚而又分不止幾十次,但這次,他哭了。我知道,在生生死死的幾十個小時裡,我可以從容面對,但他卻不能!他承受了太多的壓力,其實他比我更堅強!
我很奇怪,回到平原後,那片雪域高原給我的感覺還是那般的美麗。我們都沒有自責自己對青藏高原的那份衝動。
我說,我不會因噎廢食,我依然痴心不改。
鄭邕說,如果是河豚,他願意以身相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