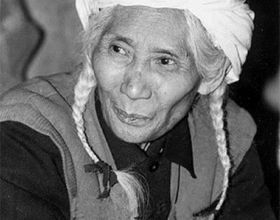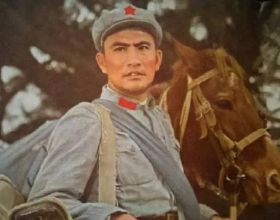“你會選什麼品種?”我轉身問萬邦斌。他是台州市乃至整個浙江省規模種植“紅美人”小苗的先驅者,至今已有8年的種植歷史。同時,也向省內外推廣了數百萬株苗木,賺足了“紅美人”的紅利期。
“理念差不多,上市時間肯定要錯開。”萬邦斌接著鄭志國的觀點介紹道:“但是我不選‘上野’,也不選‘晴姬’。‘晴姬’口感不穩定,而且容易枯水,我最討厭枯水的品種。”
不僅是“晴姬”,包括前兩年炒得很紅的“甘平”和“明日見”等品種都存在枯水的問題。2020年春,非常認可“甘平”品質的胡志藝(雨露空間創始人)從象山採購了一批果進行試銷,結果發現有枯水現象,立馬下櫃,從此對新品種敬而遠之。
“如果現在建園,我會選擇‘黃美人’,然後再搭配一些‘紅美人’和‘愛媛42’‘愛媛46’和‘愛媛50’這些品種,少量種點都是可以的。”萬邦斌說。
這幾年,萬邦斌與鄭志國、顧品等人互動頻繁,並第一時間從象山引進新品種進行觀察試種。從“甘平”到“明日見”,再到新一代的愛媛系列,最後看中的是鄭志國第二次(2012年)去日本帶回的“黃美人”。
2020年初,萬邦斌把其中10畝正值壯年的“紅美人”高接成“黃美人”,但不幸的是,在2021年初的凍害中,這批“傷筋動骨”的高接樹幾乎全軍覆沒,只剩下1行在大棚中的樹體。雖然當時樹葉盡落,但今年依然結了不少果實。
“‘黃美人’不裂果、不枯水、產量高,如果有人包園5元/斤,我把‘紅美人’全部砍了種‘黃美人’。”萬邦斌說,“‘紅美人’的缺點是成品率太低,能裝箱的只有60%左右,‘黃美人’的成品率能達到90%以上。”
“‘甘平’和‘明日見’有什麼問題?”這兩個也是他近年來重點關注的品種。
“不穩定。”萬邦斌評價道:“‘甘平’3大缺點,第一裂果,第二枯水,第三降酸慢;‘明日見’也一樣,就降酸好一點。”
“‘黃美人’也存在降酸的問題啊!”我疑問道。
2020年年底,萬邦斌曾帶我考察過鄭志國的“黃美人”表現,我對其生產效能和果實商品性都非常認可,但對其上市期頗為擔心,畢竟春節前才是水果的消費高峰,尤其是對浙江“紅美人”所形成的禮品市場來說,春節後才能脫酸上市的品種難有大的作為。
“今年降酸早,1個月前就不酸了。”萬邦斌說:“就算到二三月份賣,賣到五一也沒事,它可以賣到親民價,產地批發價在5~6元/斤之間,零售端賣10元/斤。”
“廣西‘沃柑’現在的產地價只有2元/斤左右,‘砂糖橘’1元多/斤,這才是親民價。”我笑著說。也正因為這兩個天量單品的存在,我對所有晚熟柑橘品種都心存顧慮。
“2元/斤也沒關係啊,有利潤就行了。”萬邦斌說:“像‘紅美人’一樣很多人都想走高階市場,再過兩年高階市場走不了了。”
“如果去廣西或者雲南發展‘黃美人’,你去不去?”我追問道。
與浙江相比,我認為這個品種在“沃柑”適栽區會更有發展前途。而萬邦斌也有“走出去”的行動,2017年在貴州發展了幾百畝的“紅美人”,只是選錯了地方,成熟季陰雨綿綿,品質不佳,效益自然不盡人意。
“沒什麼價值。”萬邦斌搖了搖頭說:“去廣西、雲南這些柑橘主產區,你做不了精品,種普通的沒意思。我北京有個朋友有幾百個溫室大棚,一直叫我拉些新品種去嘗試一下,‘紅美人’‘黃美人’‘明日見’都種一些,這個我倒覺得是可以的……”
我笑了笑,人總是矛盾的,雖然嘴巴說2元/斤沒關係,但心裡還是想著20元/斤甚至更高的價格。
“你家裡的‘紅美人’哪一年的效益最好?”我詢問道。
“這三四年都不錯,去年最好,一畝地4萬元多點。”萬邦斌笑著說:“去年大家都凍了,就剩我一家,只要是沒爛的果子,不管多難看,全部作精品果賣掉了。”
“那效益還可以啊!”他從2017年開始大量投產,好果的價格一直穩定在15~20元/斤之間。
“種‘紅美人’太累了,沒意思。”萬邦斌嘆息道:“如果不算苗木的收入,其實沒掙什麼錢。”
“你哪一年苗賣得最多?”我好奇地問道。這也是判斷轉折期的一個重要指標,就像2021年“陽光玫瑰”葡萄苗木出現脫銷,就基本上宣告了這個品種紅利期的結束。
“2019年賣得最多,2020年就少了。”萬邦斌說。
“轉折期是2019年。”我找到了這個時間點。
“對,從2020年開始我就不看好‘紅美人’了。”萬邦斌說:“明年‘紅美人’的日子會更難過,這兩年閩北的發展速度很快,也都採用大棚栽培,對浙江‘紅美人’的影響是最大的。”
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個新產區。從萬邦斌的苗木銷地來看,江西、湖北和湖南是“紅美人”發展最多的省份,再加上已經成氣候的四川產區,“紅美人”已然成為長江流域柑橘產區發展最快、分佈最廣的柑橘新品。
“你覺得‘紅美人’的價格還能撐得住嗎?”我舊話重提。在春節前走訪的兩個案例中,嘉興的胡曉海採用主動降價的方式儘早出貨,而象山的洪增米則採用“死撐”的方式,並以“湧泉蜜橘”為標杆,堅信10年後仍然還能賣出30元/斤的高價。
“高價越來越難賣了,‘紅美人’最終要回到親民價的。”萬邦斌坦言道:“我估計以後送禮不會送‘紅美人’了,因為東西越來越多,價格越來越便宜,已經不稀罕了。現在送禮基本上都是送外地的,沒吃過的人還是覺得好吃的,但對我們這些人來說,包括我的朋友,都已經吃了五六年了,也吃厭了。徐建國(原浙江柑橘研究所副所長)說過一句話,‘紅美人’的技術還沒搞成熟,就已經走下坡路了。”
“那還有出路嗎?”我想起那些跟風進場的種植者,即便在象山,仍有不少規模種植者還沒有回本。
“唯一的出路就是做精,種5畝10畝,兩夫妻自己乾的,還是有利潤的。”萬邦斌舉例道,“我在臺州見過一家‘紅美人’管得最好的,13畝地,能賣十幾萬元一畝。他一棵樹要吊200多根繩子,種‘紅美人’不能讓枝葉擋住果,凡是擋住果,藥噴不到位就不行……”
這顯然不是萬邦斌的選擇項。他經常抱怨做農業太累,而且被困住手腳,所以前幾年我向他建議,管好眼前這幾十畝“紅美人”,可能比在外面瞎折騰的效益來得更穩定些的時候,他的內心是拒絕的,他更希望能像我一樣走南闖北,找到更好的投資機會。
回到8年前,萬邦斌是在一個偶爾的機會中接觸到“紅美人”。他從造船行業轉投農業本來是看中大棚楊梅的專案,在購買楊梅樹時從苗販子那裡嚐到“紅美人”,隨即買下全部苗木,種下這個尚未紅起來的新品種。從2015年的“土豪橘”,到去年出現的“紅美人”滯銷,不過6年時間。
“在這種形勢下,你覺得投資農業還有沒有價值?”我問眼前這位砸對品種的老鄉。
“我覺得還是有價值的。”萬邦斌說:“現在基本農田保護了,不能新種,如果還有地能種柑橘我還會種。”
跟萬邦斌一樣,很多人都把非糧化政策當作水果產業的利好,我卻不以為然,因為前10年的快速發展導致種植面積的基數很高,即便現在剎車,後續起碼需要5~10年的消化期,才能真正達到相對合理的供求關係。
“再加上,如果品種選錯了,一腳踩空……”我提醒道。
“所以現在復耕我也無所謂,80畝地復耕也能拿回100多萬元的補償。”萬邦斌說。
“這倒是一個利好。”我笑一笑,隨便問道:“如果不做農業會去幹什麼呢?”
“不幹了,退休釣魚去。”萬邦斌說。
2022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