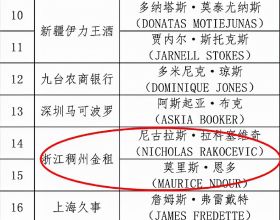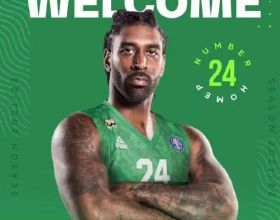小時候,盼著放寒假,一放寒假就進入過年預備狀態。
對臘八粥的眷念很淡,倒是臘月十五前後兩三天印象深刻。每年的這幾天,村裡的磨麵坊很忙,村民都在磨黃米麵。新磨的黃米麵熱騰騰、潮糯糯,多放一兩天就會發黴,所以大家都趕在這幾天蒸年糕。
蒸年糕這天,姥姥家所有人全部到位,既熱鬧又有秩序。姥姥負責人員調配和技術支援,長及腳踝的圍裙像戰袍,跟著姥姥征戰鍋臺許多年,上面洗不淨的油漬像勳章,見證了這個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辛苦幹練的一生。
碩大的蒸鍋坐在土爐子上,蒸屜上鋪著潔淨的籠布,灶臺旁邊是個巨大的鍋臺,功能之強大不亞於現在的整體廚房。鍋臺上平放著長長的案板,已經塗好了一層明亮亮的麻油——我靠近鍋臺,麻油的香味兒沁入心脾,味覺的記憶就這樣深深烙進童年裡。
裡間的火炕上坐著家裡所有的女人,她們圍著大笸籮把黃米麵搓成一個個鬆軟且有韌性的小球兒。姥姥和舅舅抬起笸籮到外間擱在鍋臺上,然後姥姥把小面球兒均勻地撒在冒著蒸汽的籠布上,籠布包好,蓋蓋兒。據說這個撒是個技術活兒,所以一直是由姥姥做,舅舅負責拉風箱燒火。火苗貪婪地舔著鍋底,蒸汽越來越大,到後來,外間騰雲駕霧,像《西遊記》裡成仙的幻境。這個過程叫蒸糕。
姥姥一聲令下,出鍋!舅舅和姥姥把冒著極大熱氣的籠布抬到抹了油的案板上。原來的面球兒已經粘在一起,姥姥則把手伸進冷水盆,蘸著涼水在溫度極高的麵糰上使勁按壓,這個過程叫搋糕,糕勁道不勁道大多看這個過程。那時候姥姥搋糕的動作行雲流水,絕不拖泥帶水。隨著糕的溫度降下來,外層便結了一層薄薄的漿皮,看起來光滑又溫順。搋好的糕叫面性糕,透著金晃晃的亮光,饞嘴的就可以就著辣湯嚐嚐了。
糕體放進笸籮,抬回裡間,給正在閒話的女人,她們負責把糕體加工成或圓或長的餡兒糕:有糖的、有水蘿蔔的、有豆沙的、有爛豆腐的,也有實心的。這個過程叫捏糕。
緊接著,捏好的糕再透過大笸籮抬到外間。原來的大蒸鍋功成身退,換上一口半大鐵鍋,裡面的液體寵辱不驚,細碎的氣泡從升起到消散從容不迫,糕一下去便迅速被裹上一層細密的脆皮——外焦裡嫩。這個過程叫炸糕。炸好的糕躺進黑亮的瓷盆裡,嘶嘶地冒著油花,頗有些不甘心的勁頭兒。
這時候姥姥站在門口喊一嗓子,孩子們便停下所有遊戲,圍過來等待任務。姥姥把炸好的糕放進白瓷碗裡,有的11個,有的13個,都是單數,指揮孩子給相好的親戚鄰居送去。這是送糕。
之後,跑得滿頭大汗的孩子,累得人困馬乏的大人,還有姥姥這個大功臣,聚在一起吃年糕。媽媽愛吃麵性糕,姐姐愛吃實心糕,我愛吃蘿蔔餡兒糕……吃了年糕意味著這一年順利圓滿,下一年還會步步登高。
我至今仍能清楚地記得煙霧繚繞的屋子,喜笑顏開的家人,尤其記得姥姥裡外指揮大家忙碌的樣子,這個過程,讓我看到了家以及家裡生活的煙火氣。
(作者單位系河北省懷來縣沙城鎮第四小學)
《中國教師報》2022年01月19日第16版
作者:張洵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