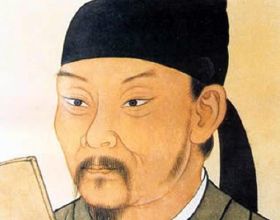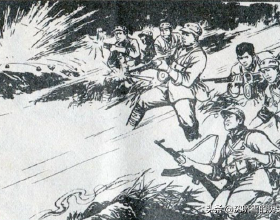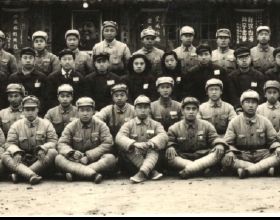中文導報 東瀛歲月
作者:懸浮物
《你好李煥英》在日本主流院線上線,大概是這5年來這個國家對我最大溫情了。
電影在日比谷東放的影院的最不起眼的地下1層小廳上映,因為哭著笑著,眼睛始終對焦模糊,也正好朦朦朧朧假裝身臨其境,回到我80年代的童年期。疫情以來久久回不去堆壘的鄉愁,人到中年時候既為人母亦為人女的雙重身份代入,以及對一去不返的類似橋段的喚起,李煥英變成一個複雜而華麗的“淚光閃閃節”。
各種淚點不待贅述。
對於這樣的作品,其實寫影評也沒啥意思。拿什麼去評判呢?劇情是沒有邏輯的。要邏輯幹什麼呢?親情,尤其是母子之情,不說全部吧,大一半是沒邏輯的。母愛驅動力,不需要理由。以前有個熱播的劇那句名言,說,家,不是講理的地方。其實這話,放在李煥英身上,放在母親的愛上,也許更確切。
我們明知道劇情框架粗糙不堪一擊,可我們就是吃這一套。這不是影評的責任區,而是被觸動了內心的柔軟,而想要為它自圓其說,這其實是我們對自己表現的憐惜。我們在匆忙的充滿不可調和的矛盾不可克服的苦難的日常之中,誰像媽媽那樣,一直不動聲色地陪跑,一邊抱怨著數落著罵著你個小王八蛋,一邊用盡力氣護犢子勒令你只要!只要!只要健健康康快快樂樂就好啊。
除了媽媽,沒有別人了。到長大,尤其為人母,到漂到海外,尤其回不去的時候,更加清楚了。
所以李煥英不是什麼好電影,那是如同把你我的柔弱,作為孩子一般,需要撒嬌,需要人包容,需要寵溺的內心需求喚醒了的神奇魔咒。渴望無條件的愛與支援,在現實中需要好多的說辭,但在電影裡,這種義無反顧的“陪伴”,那麼自然,一氣呵成。那不就是我們渴望,然而離開母親以後不可能再得到的嘛。
這種共情,以母愛的形式展現,卻絕對不止於母愛一面。原來我一直是在被呵護著,自以為是幕後,卻是別人眼裡的臺前,做著配角,其實被捧成主角,我的身邊竟然有這樣鞍前馬後、默默無聞的犧牲者!誰不希望這樣,誰不會為此而感動——這其實是疲憊的我們真正的點。
說什麼也是多餘。
工於詞藻的讚美不適合評價李煥英,更配不上歌頌母親。今天單曲迴圈了那首片尾的《依蘭愛情故事》。我覺得這樣帶著土味的大白話,二人轉的喜感和小調的略微憂鬱感,更能傳達愛的真諦。粗糙平淡中,喜樂摻雜苦悶,可不就是我們回頭看終將覺得,正如李煥英說的那樣的,“我覺得我這輩子很幸福”的,歲歲年年。
《依蘭愛情故事》
老妹兒啊 你等會兒啊 咱倆破個悶兒啊
你猜那 我心裡兒啊 裝的是哪個人兒啊
美女兒啊 屌絲兒啊 整不到一塊堆兒啊
啥人兒啊 就啥命兒啊 咱倆就湊一對兒吧
你一笑啊 我刺撓啊 渾身都得勁兒啊
你一哭啊 我膽兒突啊 就掐我消消氣兒吧
情人兒啊 給個信兒啊 咱倆啥前兒辦事兒啊
一百年兒 一輩子兒啊 情願我笑你呆兒啊
我活著是你的人兒啊 死了是你的鬼兒啊
你想咋地兒就咋地兒啊
月亮它照牆根兒啊 我為你唱小曲兒啊
看你睡啦 我心裡美滋味兒啊
媳婦兒啊 進門兒啊 咱倆過日子兒啊
我有情啊 你有意啊 生了個胖閨女兒啊
雞毛啊 蒜皮兒啊 那都是我的事兒啊
你摟寶兒啊 座屜兒啊 天天都有局兒啊
誰家的 爺們兒啊 藏進下屋碗架櫃兒啊
你紅啦 我綠兒啊 你還罵我沒出息兒啊
扔下孩子兒 你一轉身兒 從此跑沒音兒啊
唉 小妮兒啊 我寶貝兒啊
看來咱倆才是一對兒啊
我活著是你的人兒啊 死了是你的鬼兒啊
你想咋地兒就咋地兒啊
月亮它照牆根兒啊 我為你唱小曲兒啊
看你睡啦 我心裡美滋味兒
我活著是你地人兒啊 死了是你的鬼兒啊
你想咋地兒就咋地兒啊
太陽又升一輪兒啊 映透了窗戶紙兒啊
看你醒啦 我心裡沒滋味兒啊
日子長啊 我為你擦眼淚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