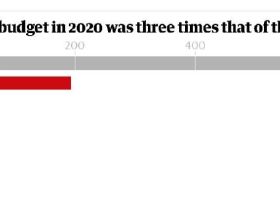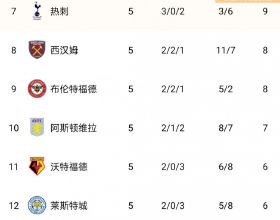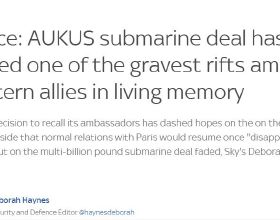"吃人的事,對麼?"他仍然笑著說,"不是荒年,怎麼會吃人。"我立刻就曉得,他也是一夥,喜歡吃人的;便自勇氣百倍,偏要問他。
......
"從來如此,便對麼?"
"我不同你講這些道理;總之你不該說,你說便是你錯!"
以上內容,估計很多人都知道,它摘自於中國現代第一部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作者是魯迅先生。
執政府前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群兩君開追悼會的那一天,我獨在禮堂外徘徊,遇見程君,前來問我道,“先生可曾為劉和珍寫了一點什麼沒有?”我說“沒有”。她就正告我,“先生還是寫一點罷,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
這段文字同樣摘自於魯迅先生的《記念劉和珍君》。
對於我這樣被朋友們標籤化為“眼裡揉不得沙子”的人,關於徐州豐縣事件,我竟然隻字未寫,個別朋友感覺不適應。
我該說點什麼。
說心裡話,這件事我知道大致前因後果後,一時真的不知道說什麼。我不說什麼,不是說我膽小了,遇事不敢說話了;不是說我麻木了,見到醜陋不敢伸張正義。
我之所以沒寫,那是因為,關於農村婦女拐賣的報告文學太多了。
除了網上炒得很熱的,34年前江蘇作家寫的那個調查報告,我還看到了《北京文學》2016年第9期的《疼痛的農村-“越南媳婦”出逃前後調查》,寫的是2014年末,河北邯鄲116名“越南媳婦”集體出逃。這篇報告文學中提到了在以江蘇徐州為中心的蘇皖豫交界地區婦女被拐賣現象非常嚴重。河北邯鄲“越南媳婦”集體出逃的組織者叫吳美玉,她是20多年前被賣到邯鄲的越南女人,在邯鄲已經生兒育女。後來,夫家讓其回越南探親,她原本想回到越南後就不再回來,沒想到的是,她的越南家人又將其轉賣到其他地方,萬般無奈之下,她尋求夫家幫助,這才再次回到邯鄲。
我沒有寫這件事,主要是因為,事件的進展中有熱心的記者和正義感的人士在努力尋找蛛絲馬跡,他們佈下天羅地網收集犯罪證據,很多愛心人士主動幫助聯絡和核實資訊。在現在這樣的風口浪尖上,過多不利於案情分析推進的議論文字會沖淡或者稀釋主流的聲音。
對於我等只有熱血沒有能力的人,只要隨時站在那幾個勇敢者的後面,給他們搖旗吶喊、助威鼓勁即可。我就是寫,也就寫寫不著邊際的鼓勵文字,別的我好像什麼也做不了。在無所作為的情況下,不給有作為的人添亂,其實也是一種作為。
此外,我還有一重考慮是,透過豐縣的個案是否可以回溯出源頭,以便有關部門一攬子根治這個惡疾?記得以前打擊拐賣兒童案,結果,民警把被拐賣兒童送回家鄉之後,孩子的親生父母不置可否,因為,他們沒有比主家更好的撫養孩子的能力,甚至有孩子再次跑回到買孩子的人家。
一時之間,我的腦子非常混亂。
對於徐州豐縣的那個作惡者,我覺得食肉寢皮都不過分。現在最關鍵的問題是,將惡人碎屍萬段之後,殘局還是要有人收拾,我不知道誰有更好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很多人估計也有跟我一樣的擔心,可法律還是要解決不公平、不公正的問題。我們是否有刮骨療毒的能力和勇氣,我一時沒有了答案。
這不是我一個人沒有答案,很多當事人都以沒有答案而失去察錯防弊的能力。
大眾與我一樣,當聽到那位鐵鏈女說出“這個世界不要俺了!”時,我們都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只有絕望到什麼程度的人,才能說出如此悲天憫人的話呢?從鐵鏈女的這句話中,“如果你感受到痛苦,那麼你還活著;如果你感受到他人的痛苦,那麼你才是人。”這句話是俄國大作家列夫·托爾斯泰說的。
事件曝光之後,網上有人寫了很多震撼心靈的段子,最震撼我的一句是“你與鐵鏈女之間的距離不過是一悶棍。”我是一個女孩的父親,這句話讓我不寒而慄!
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這雖然於鐵鏈女毫不相干,但在於芸芸眾生,卻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只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我不知道,這是不是那些有可能改變鐵鏈女人生的人間。
真的猛士,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可惜我不是猛士,最多不過是暴力一悶棍下的犧牲品而已。面對某些人的無能為力,面對一些當事人的習以為常。
我也想糾纏著這些人問一句“從來如此,便對麼?”